
《生命的尺度:从海德格尔到阿甘本的技术和生命政治》,[美]提摩太·C. 坎贝尔著,蓝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288页,78.00元
美国哲学家提摩太·坎贝尔(Timothy C. Campbell)新近被翻译为中文的著作《生命的尺度:从海德格尔到阿甘本的技术和生命政治》重新思考了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生命政治。他考察的主题是:技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与生命交织在一起。作者在切入主题之前首先回应了生命政治在今天遭遇的难题,它深陷死亡政治的漩涡,在其中野蛮生长,且“对具体的威胁毫不关心”。生命政治难题构成了坎贝尔这本书所讨论的核心问题:若生命政治天然倾向于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其理论价值何在?坎贝尔在序言中给出了一个论断,“当代生命政治天衣无缝地蜕化成死亡政治的原因在于,我们要面对尚未被探索的技艺和死亡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似乎贯穿了多个以生命政治为关键词的当今最重要的哲学家的著作”,因此坎贝尔指出,当代生命政治的困境源于技术与死亡(thanatos)的隐秘关联。
生命的“划界”:正当与不正当
坎贝尔的论述始于一个看似简单却影响深远的哲学区分:海德格尔对“本真”(eigentlich)与“非本真”(uneigentlich)的思考。在《生命的尺度》开篇,作者敏锐地指出,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和埃斯波西托对这两个术语的翻译并非传统的“本真/非本真”,而是采用了“正当/不正当”(proper/improper)的译法。这一语言学选择打开了理解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新维度,技术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正当性”的问题。从海德格尔到阿甘本,哲学家们不约而同地将技术视为存在论撕裂的根源,技术通过“正当”与“不正当”的划分,将生命区分为值得保存的“本真存在”与可被牺牲的“赤裸生命”。这种划分并非偶然,而是根植于西方哲学对“技术”的本体论思考,技术既是存在的揭示者,又是存在的遮蔽者,其双重性使得生命政治始终徘徊在救赎与毁灭的边缘。因此,坎贝尔通过意大利理论家阿甘本、埃斯波西托对海德格尔的解读,将“本真/非本真”的存在论区分转化为“正当/不正当”的生命政治范畴。这一转化揭示了一个核心命题,技术对生命的规训,本质上是通过书写、语言、装置等中介,将生命纳入“正当性”的判断框架来实现的,而那些被标记为“不正当”的生命,则成为政治暴力的潜在对象。生命的划界在正当与不正当的区分中完成,同时,随着现代不正当写作成为标准,存在问题也衍生出规范化的结果。
坎贝尔基于技术对生命开展的正当与非正当分析,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福柯的老师康吉莱姆,作为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史家,他在《正常与病态》这部著作中基于医学的分析对生命进行了“正常/病态”的划分。康吉莱姆对生命的划界来自法国独特的认识论传统,在“巴什拉—康吉莱姆”认识论断裂框架中,生命的划界并非来自外在的强制性力量,而是来自生命自身蕴含的规范。坎贝尔在这本书中所做的分析不同于康氏在生物学意义上所展开的讨论,他通过技术架构了一种新的生命政治分析框架,在从“本真/非本真”向“正当/非正当”的跨越中找到了生命政治陷入死亡政治的密码,并力图将其解救出来,最终走向一种积极的围绕生命实践而展开的生命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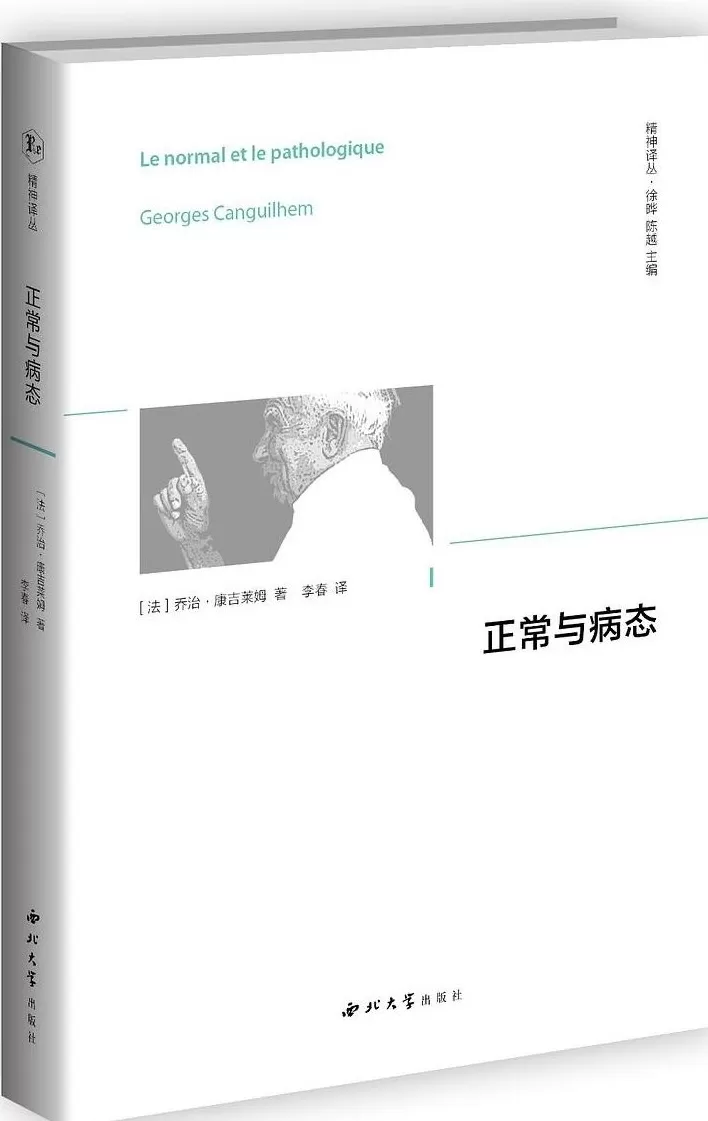
康吉莱姆著《正常与病态》
全书共分为五个部分:序言指明了这本专著讨论的主题及其核心任务。第一章主要讨论海德格尔的生命政治学,基于《巴门尼德》(1942-1943年讲稿)、《技术的追问》(1954)以及《人道主义书信》(1957)来讨论海德格尔晚期思想中技术与生命政治的交集。在第二章中,作者从海德格尔过渡到阿甘本与埃斯波西托,讨论阿甘本对安济(oikonomia)下的装置(dispositif)功能的思考,解读埃斯波西托对装置和人格的理解。第三章主要聚焦于彼得·斯洛特戴克,讨论海德格尔的形象如何出现在人性化和兽性化媒体的区分中。在第四章中,作者在对生命政治已经被死亡中的技术印记撕裂的谱系学进行分析后,转向了生命实践。他通过福柯的文本《安全、领土与人口》《主体解释学》来定位生命权力的谱系,并以此为基础,“通过注意力和游玩的范畴描绘出生命的实践,来回应福柯认为自我要为今天的生命权力负责任的诊断”。
海德格尔:技术与生命政治
第一章《正当的区分》聚焦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揭示其思想中隐含的生命政治维度。坎贝尔通过解析《巴门尼德》《技术的追问》等文本,指出海德格尔对“手写”与“打字机书写”的区分及其决定性意义,手写被视为“正当的”存在论行为,它通过手与语言的共生关系,维系着人对存在的本真关联;而打字机则将书写从手的“本质领域”撕裂,使语言沦为交流工具,最终导致所有人都变得“千篇一律”。这种技术批判延伸至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诊断。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将现代技术本质定义为“集置”(Gestell)时,不仅揭示了技术对自然的“促逼”(Herausfordern),更预言了一种新型生命政治的出现。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是一种暴力性的解蔽方式,它“要求开采自然中蕴含的能源,开采就是运输,运输就是储藏,储藏就是为了分配,分配就是交换”。这种解蔽的链条永不终结,形成了一套自我维持的封闭系统,最终将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都转化为随时可被提取的“持存”(Bestand)。这种技术框架不仅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更深刻地重构了生命本身,当生命被纳入技术秩序,它便不再是目的,而成为可管理、可优化的对象,人由此沦为技术的附庸。坎贝尔强调,海德格尔的焦虑不仅在于技术对存在的遮蔽,更在于其政治后果,它揭示了技术如何成为划分生命价值、决定生死界限的根本机制,为生命政治中的排斥机制提供了存在论基础。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未被揭示的生命政治,技术通过划分“正当”与“不正当”的存在方式,构建了一套潜在的死亡政治逻辑,那些无法维系与存在本真关联的生命,终将被纳入技术的统治秩序,成为可被牺牲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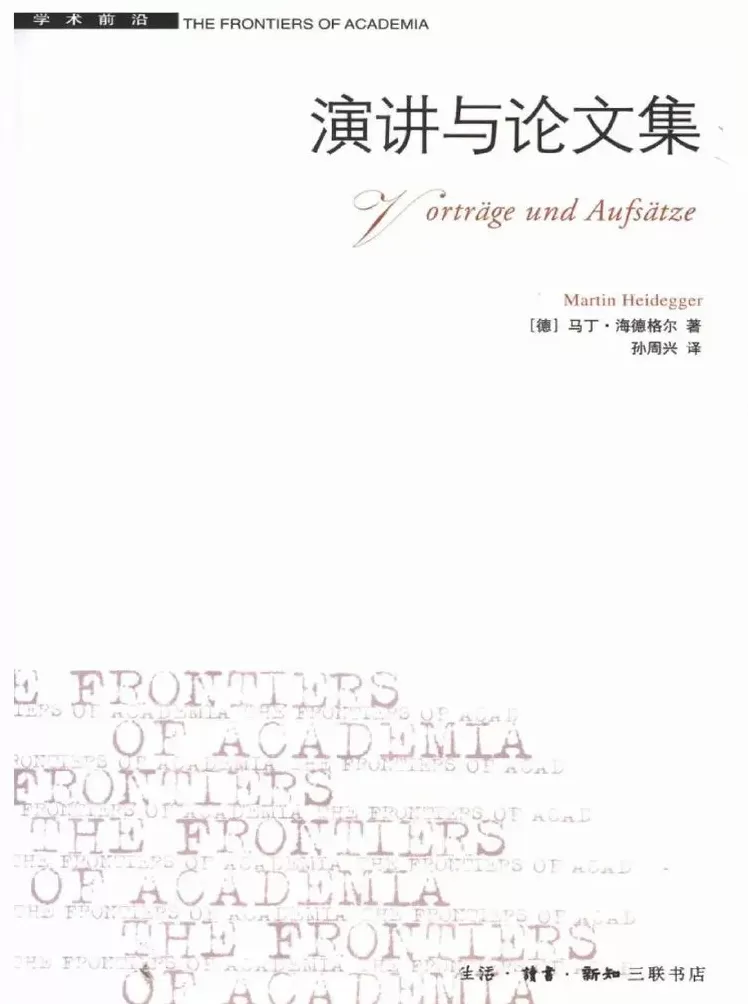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
死亡政治学:死亡装置与肯定装置
坎贝尔在这部著作中做出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在于,他系统性地揭示了阿甘本生命政治学与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内在对话关系。第二章指出,阿甘本在《神圣人》中提出的核心概念“赤裸生命”(bare life),正是海德格尔“持存”概念在政治领域的拓展。坎贝尔在《生命的尺度》中用大量篇幅分析了阿甘本如何将海德格尔的“正当/不正当”框架转化为赤裸生命与政治生命的对立,并最终发展出一套关于现代性作为永恒死亡政治的论述。阿甘本对zoē和bios的著名区分,在坎贝尔的解读中呈现出新的理论深度。这一区分不仅仅是概念性的,它还揭示了现代权力如何通过将生命降级为zoē而使其可被杀死。坎贝尔特别关注阿甘本思想中“装置”概念的核心地位。通过分析《什么是装置?》和《王国与荣耀》等文本,他指出阿甘本将装置理解为一种捕获、定向、控制生命姿态和行为的机器,其根源可以追溯至基督教神学中的“安济”概念。他对阿甘本引入神学解读生命政治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上帝治理是一种原始装置,现代生命治理的装置就是原始装置现代性的变种,“神圣人与今天的当代人重叠在一起”,现代生命被日益密集的装置网络捕获。关键在于,这些装置不仅控制生命,更生产主体性。尽管阿甘本在对福柯的解读中给出了一个立场,“技术不可避免地导致生命只能与活着的主体化和去主体化的过程有关”,但是坎贝尔指出,阿甘本将海德格尔的正当与不正当区分放在死亡政治学视角下,“忽略了技术在人类脱离‘存在’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指出了阿甘本理论中的一个关键困境:如果将现代性完全等同于死亡政治,如果所有生命都已成为潜在的神圣人,那么抵抗的可能性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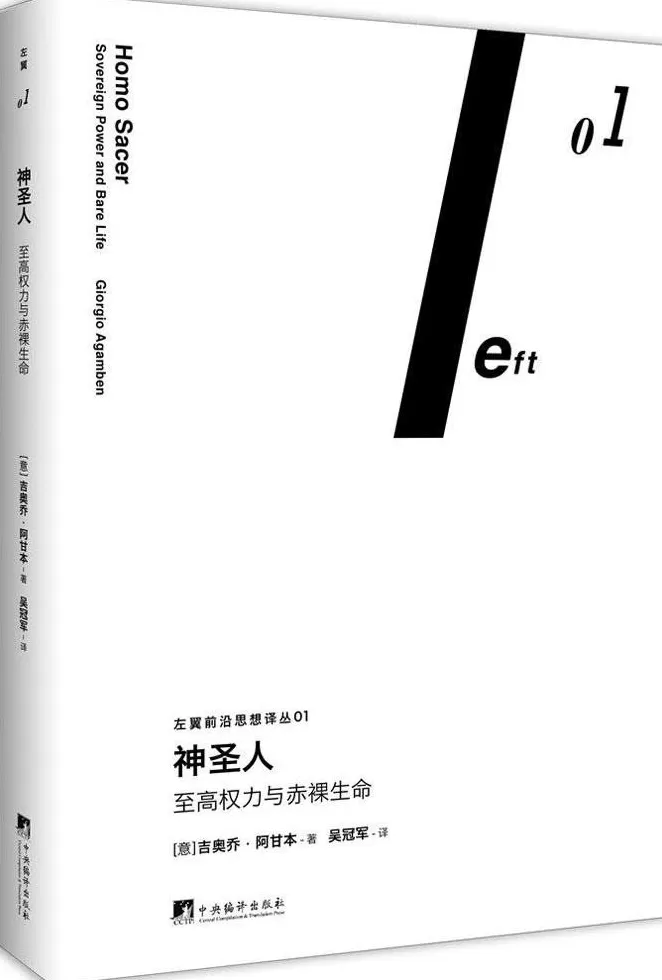
阿甘本著《神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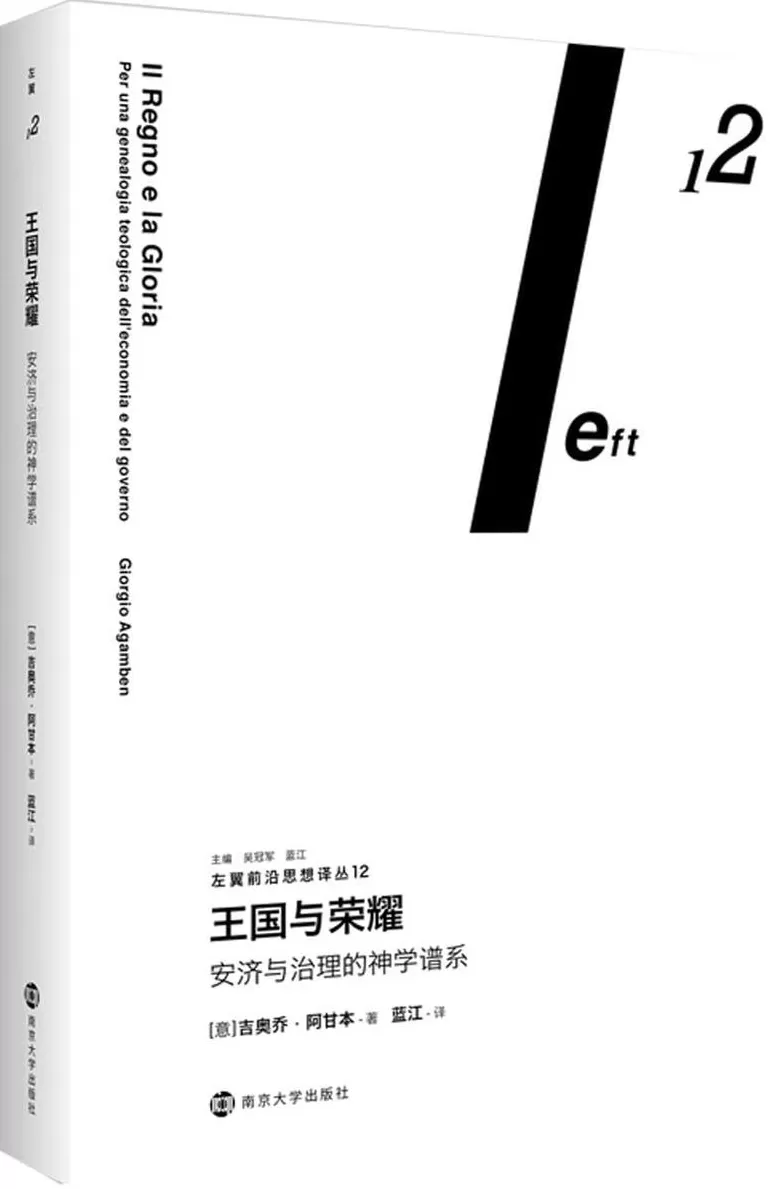
阿甘本著《王国与荣耀》
面对阿甘本似乎无解的死亡政治图景,坎贝尔转向了意大利思想家罗伯特·埃斯波西托的免疫范式(immunity paradigm),寻找生命政治新的可能,这构成了《生命的尺度》另一项重要的理论贡献。坎贝尔关注到,埃斯波西托找到了一种可以将肯定性方面重新置入当代装置角度的途径,后者通过非人格哲学来思考生命政治,对他而言,人格装置一直以来都在发挥作用。在《第三人称》中,埃斯波西托从罗马法与基督教神学中追溯“人格”(persona)的起源,指出“人格”本质上是一套区分“人”与“物”的装置。他试图通过“非人格”消解“正当”与“不正当”的二元对立,主张生命政治应超越对“个人主权”的执念,转向一种包容差异的共同体。埃斯波西托构想了一种不依赖排除逻辑的生命政治,生命不是被保护或消灭的对象,而是不断生成、变异的过程。坎贝尔认为,埃斯波西托的理论为对抗死亡政治提供了可能,技术不再仅仅是海德格尔式的“集置”或阿甘本式的死亡装置,而可能成为免疫调节的肯定装置,但这样的思考同样面临困境,“非人格”若无法与具体的政治实践结合,终将沦为抽象的哲学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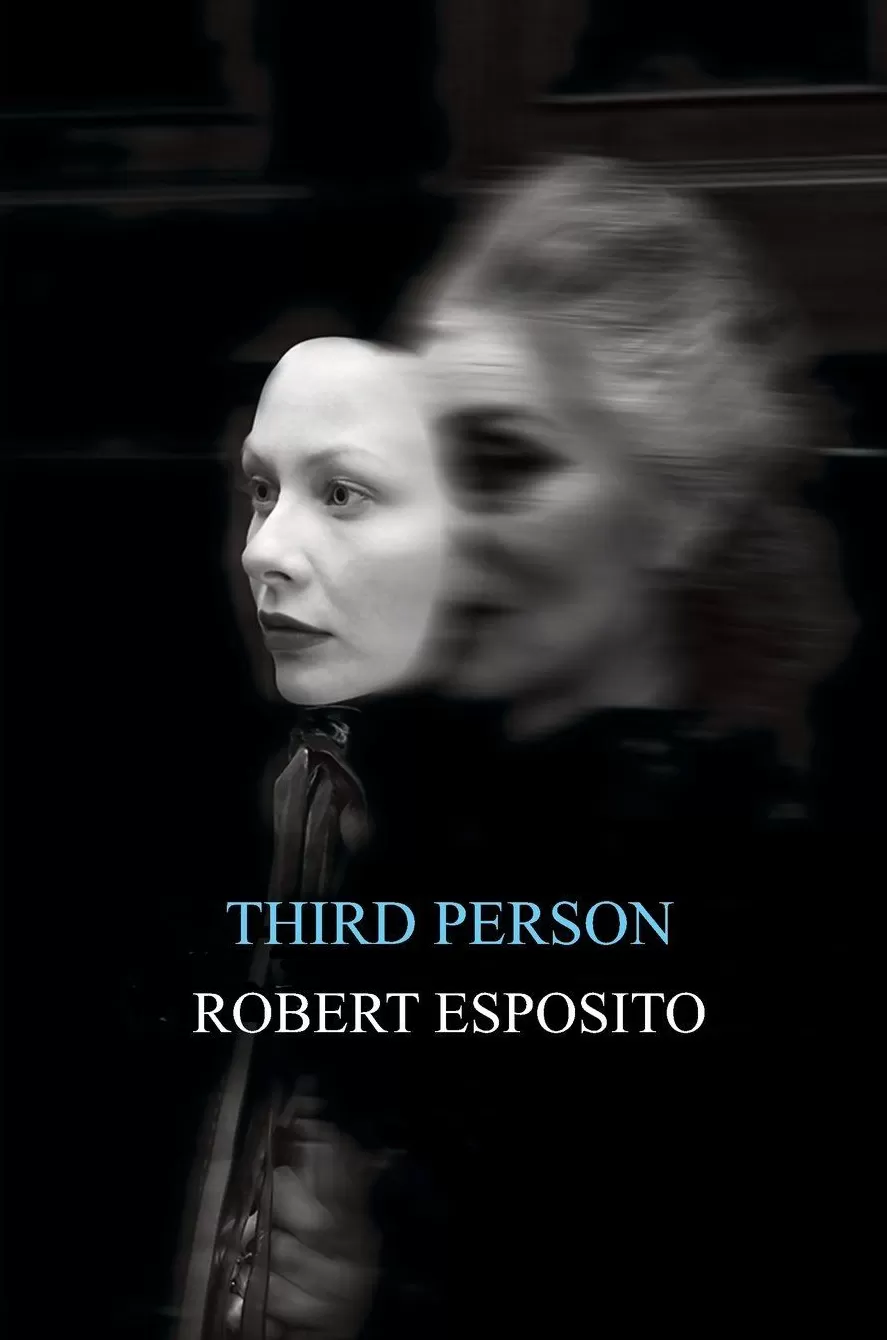
罗伯特·埃斯波西托著《第三人称》
赤裸呼吸:免疫生命政治
第三章中,坎贝尔将目光投向彼得·斯洛特戴克,称其贡献了“当今最完备的生命政治思考”。他以“免疫生命政治”为轴,揭示斯洛特戴克如何把对技术的批判推向全球化语境。通过对《球体》《空气中的恐怖》以及《愤怒与时间》等文本的解读,坎贝尔分析了斯洛特戴克如何将“免疫”(immunity)视为现代技术的核心逻辑。个体通过技术手段构建“免疫球体”,以抵御外部威胁,但这一逻辑最终导致了“共同体的死亡”与“生命的赤裸化”,个体通过技术保护自己,却丧失了与他人的本真关联。同样,今天全球化通过构建“免疫装置”,最终走向共同体的危机。坎贝尔指出,斯洛特戴克的理论暗含对现代性悖论的揭示,技术的免疫机制越发达,个体就越陷入“赤裸生命”的状态。斯洛特戴克延续了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借助“人类动物园”理论将媒体视为“驯化”人类的装置,他揭示了技术不仅是外在工具,更是人类自我塑造的环境,我们既是驯化者,也是被驯化者。在斯洛特戴克那里,“一旦共同体开始衰退,死亡政治就进入我们的视野”,同时“一旦技术扩张,最受技术威胁的就是个体”。这种循环关系暗示了技术暴力的内在性,也暗示了抵抗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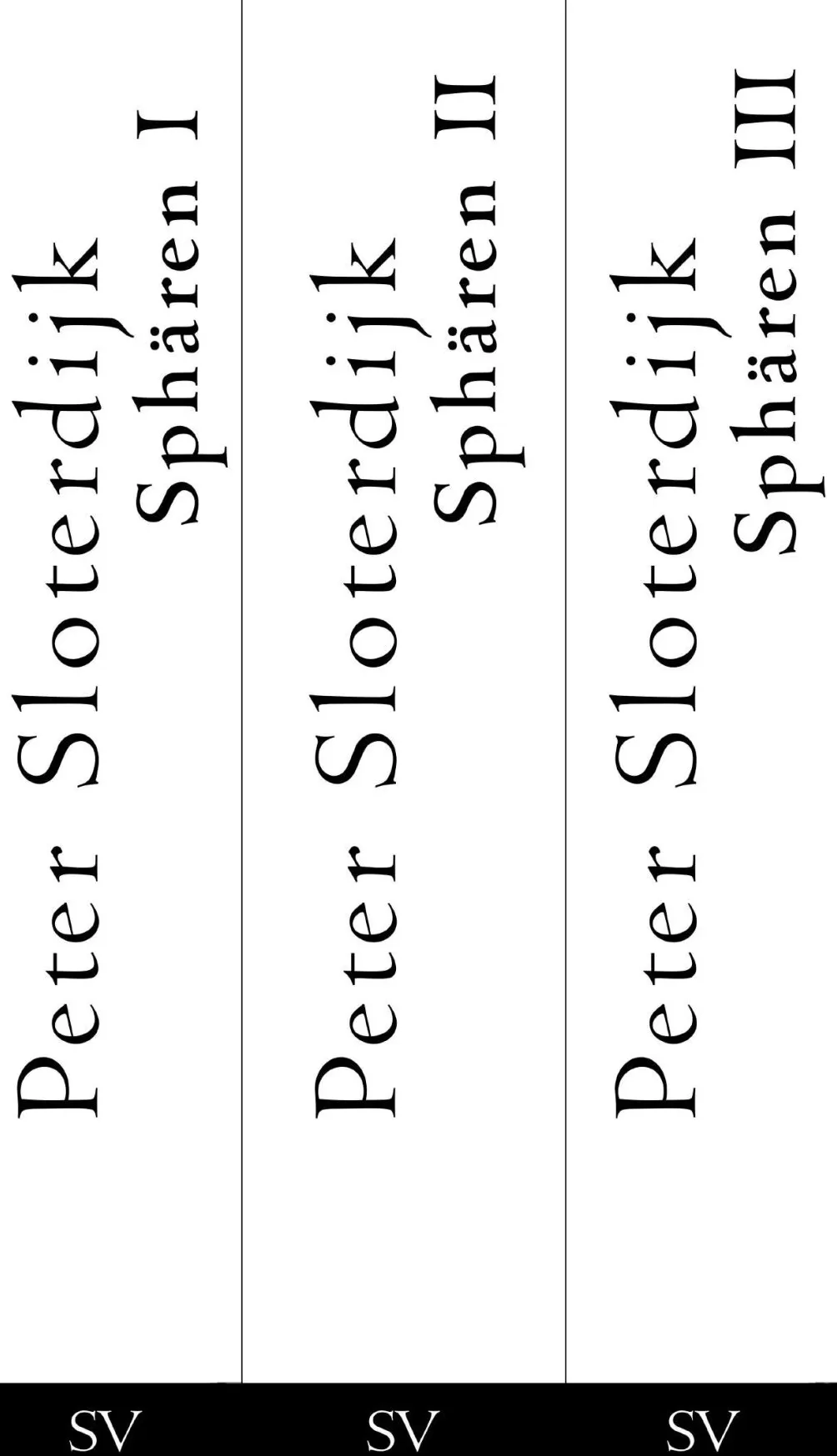
彼得·斯洛特戴克著《球体》三部曲
走向一种积极的生命政治:“注意力”与“游玩”实践
坎贝尔对福柯晚期思想的关注提供了一个将生命政治从死亡政治解脱出来的方案。他在最后一章详细考察了福柯的《主体解释学》中对“自我技艺”的探讨,并将福柯的“自我技艺”解读为一种“生命技艺”,思考技艺与生命的新的可能性。生命不再是技艺的对象,而是技艺的“实践者”。坎贝尔认为,福柯的“自我技艺”并非对技术的简单拒绝,而是将技术重新理解为一种“生命的实践”。借助福柯的理论,坎贝尔以“注意力”与“游玩”概念,提供了一种超越海德格尔式“死亡化”的可能性,通过将生命视为一种“实践的艺术”,而非技艺的对象,可以让生命重新获得“尺度”与“自由”。福柯指出“自我关怀”通常出现在不同的实践、体制和群体中,通过“不同的崇拜、治疗、知识、理论结成群体”,这意味着“个体并非在作为人类的基础上获得关怀”,自我关怀并非对自我的控制,而是对自我生命的塑造。坎贝尔结合梅洛-庞蒂的“注意力”理论与德勒兹的“在此性”概念,提出“注意力”作为一种技术,能使人在与世界的相遇中保持开放,避免将他者简化为“正当/不正当”的判断对象;而“游玩”则通过模拟、虚构等方式,打破技术对生命的固化,使生命成为“不断生成的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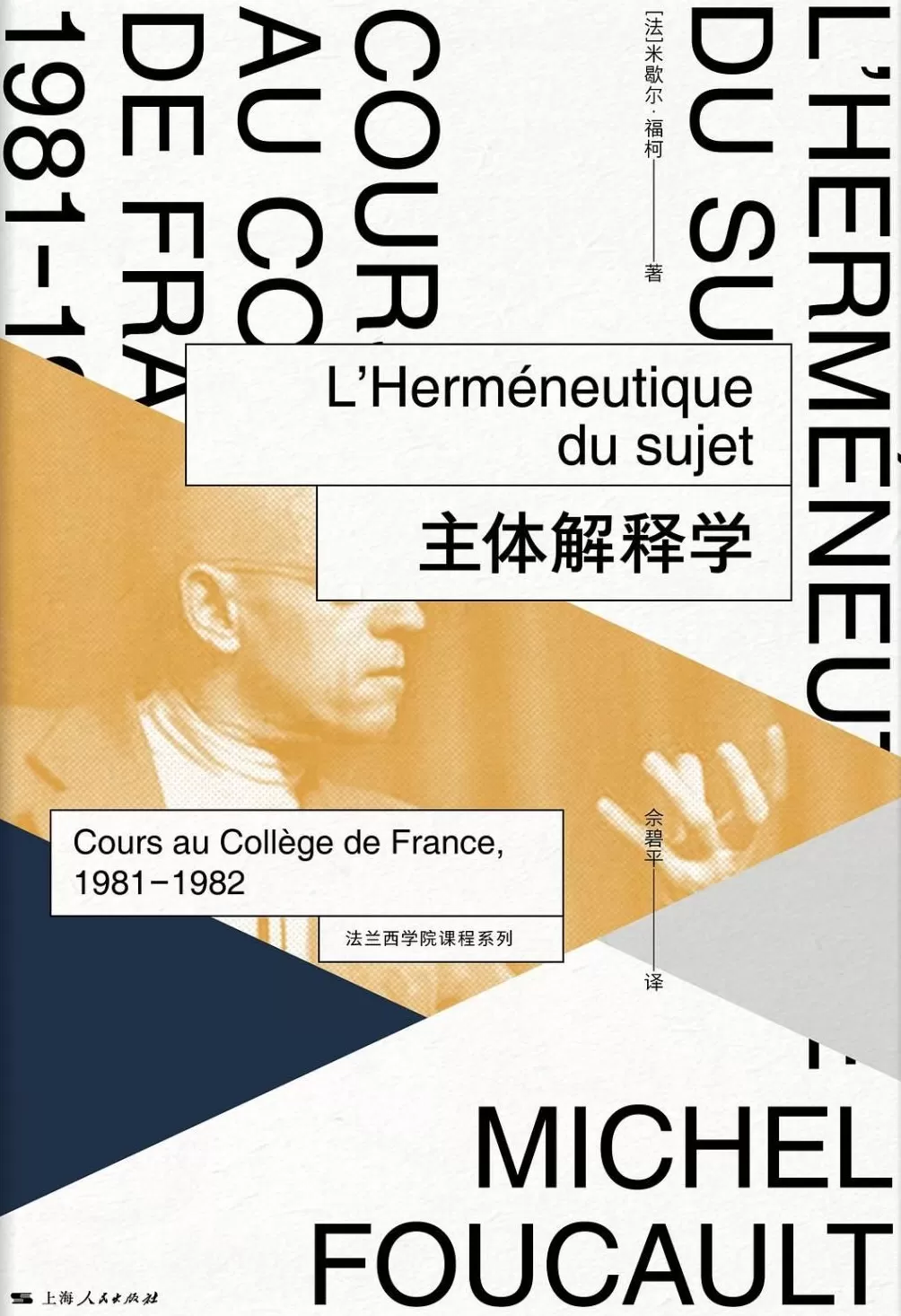
福柯著《主体解释学》
《生命的尺度》是一部极具挑战性的哲学著作,它不仅梳理了从海德格尔到阿甘本的生命政治谱系,更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死亡政治的新生命政治路径,坎贝尔的核心贡献在于揭示了技术与生命之间新的积极可能性。正如坎贝尔在结尾所言,“帮助我们在关爱与掌控之间,在我们首先从生命形式中感受到的对自我的关爱和之后才从掌控中了解到的对自我的关爱之间,找到一个缺口”,当技术成为生命的尺度,我们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暴力,也拥有前所未有的潜能。如何在这种辩证性对立中寻找出路,或许是当代政治哲学最紧迫的任务。







还木有评论哦,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