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厂生产线到AI大发展,我们正被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机器时代”。2025年11月22日晚,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机器时代》新书分享会在北京PAGEONE五道口店举行。本书作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许怡,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陈龙围绕“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谈。下文为精简版的访谈文字稿,已经许怡审定。

《机器时代》新书分享会现场
陈龙: 我们相信很多人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可能跟我有同样的困惑,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现在讨论最火的可能是AI人工智能,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怎么还会有人去写“机器时代”?《机器时代》这本书的书名有什么特殊的意涵或者所指吗?
许怡: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他就已经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机器大工业生产的阶段,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一直蔓延了几个世纪,直到现在,我们都一直处在机器大工业生产时期。我只是研究了历史长河中一个比较短暂的阶段,用这个题目可能不够严谨。但另一方面,不管是工业化早期使用的机器,还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些高度自动化的机器,它们在本质上是有共同点的,即它不仅是一种生产的工具,也是资本借以控制工人、治理工人的工具。所以用这样非常宽泛的概念作为书名,也是想跟过去历史上出现的人与机器、与技术的关系进行一些对话。
这本书里面的引言标题“自动化与机器人时代”会相对准确一些。虽然我们现在正在步入AI时代,但这本书涉及AI技术的部分不是很多,以后也许会进一步围绕这块开展一些新的研究。
陈龙:您刚刚也提到了从工业革命以来人与机器之间的对抗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您看来,相比以往,今天的机器换人有何独特之处吗?
许怡: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诞生的最主要的技术有蒸汽机、纺纱机、动力织布机等。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技术很显然已经更先进,在自动化程度上也是高出一大截,我们主要使用的是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等。如果我们去看技术本身,它确实发生了很大的飞跃,但是这两类技术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属于劳动力替代型的技术。不管是水力纺纱机、珍妮纺纱机还是动力织布机,都可以取代很多工人。我们今天所谈到的机器人也是一种劳动力替代型的技术,在这一点上面它们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技术出现的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差异。在工业革命时期,当时还处在工业化早期,一开始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后来蔓延到欧洲地区,全球范围来看工业化水平还是相当低的,也就是说,哪怕英国的工人,因为这些技术的出现暂时失业了,但是它的工业化产品输送到全世界,还是供不应求,工人的就业机会还是有很多的。反观今天所处的经济发展的阶段,我们已经迈入了比较成熟的工业化时期,从这个角度来看产能是过剩的,很多产品可能会卖不出去。
其次,在工业革命时代,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国家做了一些政策上面的调整,包括英国政府出台的《工厂法案》,这种政策调整加上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以及社会力量的介入,大大改善了当时工人的劳动条件和收入水平。但反观今天所处的时代,目前我还没有看到社会政策、社会力量比如工会在经历了机器换人这样的浪潮之后采取了什么特别清晰的举措,去保障劳动者的就业和劳动条件。
陈龙:这本书的序言是沈原老师写的,请沈原老师总体性地谈一谈对这本书的评价。
沈原:今天上午我们在北大开会,邱泽奇老师是技术社会学的顶尖专家,他提到说我们现在进入一个人机时代,就是人类和机器,怎么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许怡是在劳工社会学圈里第一次写作了这样一个著作,把我们领向这个问题。
我是老派人物,从我的立场上看这本书,首先会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于机器的发展曾经抱持非常乐观的态度,他们说机器是人的手臂的延长,机器发展的结果会替代人的劳动。人脱离了劳动生产领域以后干嘛?马克思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面的回答是,上午读哲学,下午画油画,晚上有闲暇时间读诗歌或者去钓鱼,这是当时他们的一个看法,非常浪漫主义地看待工具的进展。
到了第二个阶段,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刚刚故去的劳工社会学家,是劳工社会学的奠基人,叫迈克尔·布洛维,我们曾经在这儿开过他的《生产的政治》那本书的发布会。布洛维在《生产的政治》里面专门有一节讲机器,他和布雷弗曼讨论,机器是纯洁的吗?机器是中性的吗?他用了布雷弗曼的话说,机器本身是无罪的,有罪的是它和生产关系结合起来,以至于机器变成了压迫工人的工具,所以他说机器有这样的消极的一面。那个时候布洛维用工厂民族志的办法进入到一个农机厂,他还是操作机器的,他是主体,操作机器,所以他提出了劳工的主体性。
我们现在进入人类和机器关系的第三个阶段,这时候不仅是机器生产,而且我们看到是自动化的机器,随着AI技术的发展,机器绝不仅仅是人的手臂的延长,人的脑力也外化了,而且脑力形成自我学习的能力。造成的结果就是机器对工作岗位的占位,机器把人从工作岗位上赶出去。而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像马恩浪漫主义所设计的社会浪漫,赶出去的人可以上午学哲学、下午画油画,我们是一个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当这些工人被赶出去的时候,受影响的不是他一个人,还有他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到现在都没有对这种情况作出相应的社会安排,我觉得这是我们面对的最大问题。许怡在她的书里把这个问题提给大家。这本书让我们去思考一个合理的、符合人类终极价值的人机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而现在岗位上的工人他们是如何看待机器换人这样一个现象。我们要做的是传达他们的思想和声音,是促使这个社会能够设计出一套合理的社会安排,来化解人机之间的张力。社会学从来不是理论的说教,社会学一定有它的实践干预的倾向,我们要发展这个维度,也就是布洛维说的公共社会学的维度。
陈龙:沈老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一个象征或者一个代表,它的发展是非常快的。但与此同时,在制度上我们往往是落后的。这就造成技术和制度之间有一种错位,有一种脱节,而这种错位和脱节可能就给机器换人换下来的这批人造成比较大的痛苦。
接下来把问题再抛向许怡老师,您从一开始为什么会想到做这样一个研究?
许怡:其实我很早就开始在做劳工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的也是工厂工人,到了2015年之后看到有很多关于机器换人的媒体报道,媒体上的声音基本上是一边倒的,都是在肯定这样一种趋势和做法,把引入工业机器人、自动化说成是必然的趋势,并且带来各种好处,既可以提高效率、保证生产质量,又可以解放劳动力等等。我当时对于这样一个说法持怀疑态度,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我需要亲自进工厂看一看,听听工人的说法、工人的声音。
陈龙:通过您自己的调研,您感觉机器换人的趋势,是因为时候不到,比如出于技术原因、经济成本因素,我们还不能换人,还是说人真的有一些特殊的东西是机器替代不了的?
许怡: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是存在的,一方面技术并不如我们想象中这么完美。当然会有一些所谓的技术决定论者,他们认为这只是时间问题,技术一定会慢慢改善,最后人能做的机器都能做。但至少在我的田野调查当中,我发现在某些情况下或者某些生产工艺当中,机器做得没有人这么好,包括也不见得做得比人更快,质量上面、稳定性方面做的也不如工人。
我去年在武汉调查了无人驾驶出租车的情况,前段时间再去时,发现无人出租车的运营范围又进一步扩大,以前只有市区外、三环之外一些片区是覆盖的,现在基本上只剩下市区很小的一块没有被覆盖到,外围的地方都是无人出租车的运营范围。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安排、社会政策这方面还没有跟上的话,这么快就面临技术性失业危机的话,整个社会会承受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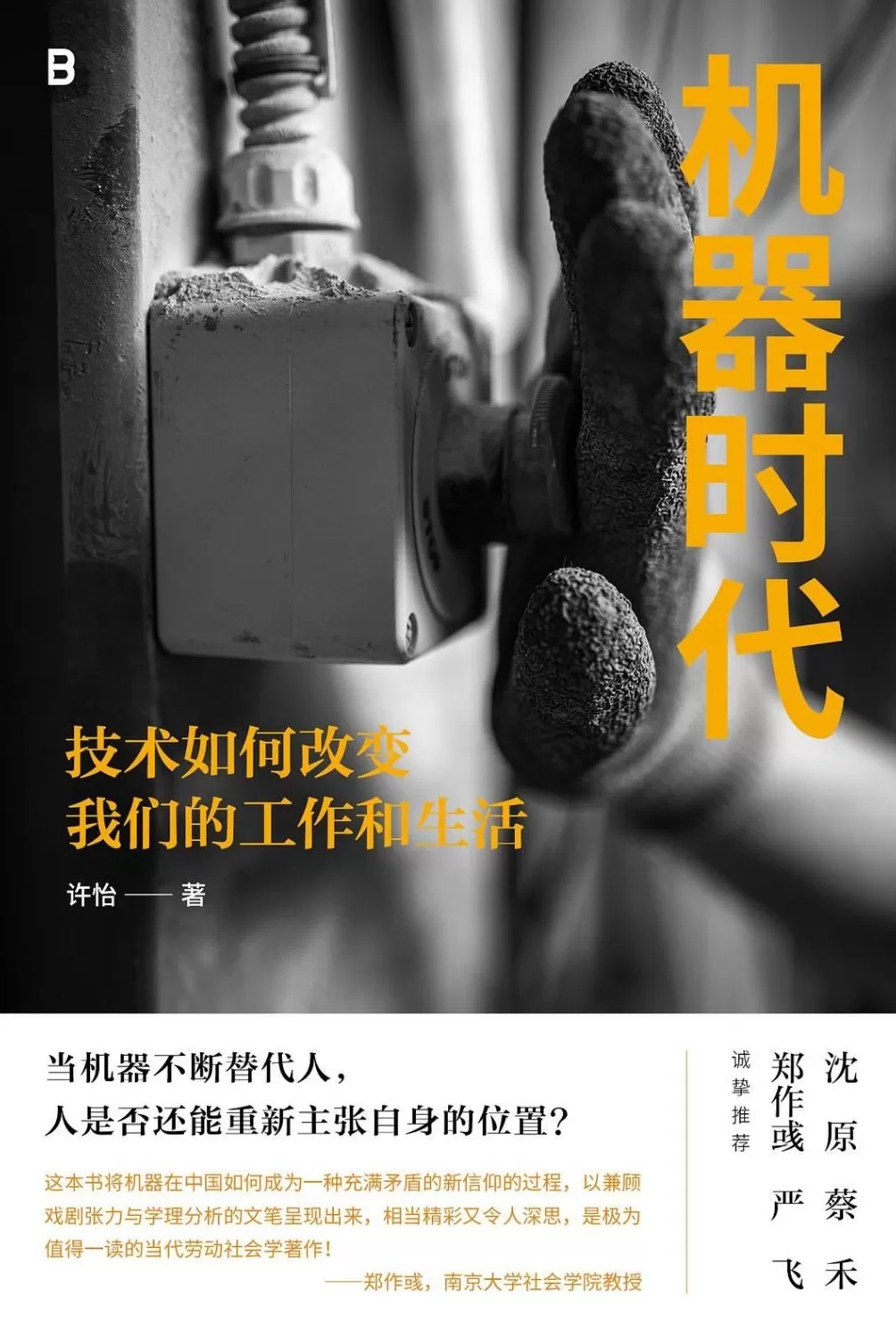
陈龙:我们都知道做劳工社会学有一个传统,叫工厂民族志或者叫参与观察,或者叫同吃同住同劳动,很多在劳工社会学领域经典的著作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完成的,许怡老师在研究过程中也做了参与观察,也到工厂里面去应聘,去做普工,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做田野的经历和过程。
许怡: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打算真的进厂里面去做流水线工人,因为我一开始没有想过存在这样的可行性。我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36岁,而往前十年,我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发现我是进不了工厂的,因为我超龄了,二〇〇几年工厂里面只招年轻的女工,一般要求25岁以下,所以我十年前就超龄了。但是等到我开始做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发现我又不超龄了,这个特别有意思。工厂里面年轻的劳动力越来越短缺,不是说总体上缺工,而是农村劳动力群体出现老龄化趋势,所以工厂已经没有那么容易招到年轻工人。当时进行一些访谈之后,我听一些工友说他们厂现在也在招暑期工,我就试着去应聘,还叫上了我的一个学生。我这个学生只有20岁,她是属于十年前最受资本青睐的、年轻的、女性劳动力。我们一起去不同的工厂应聘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跟我的学生也遭遇了区别的对待,比如我们去的第二家工厂,我们分别去工厂门口的招工岗亭,有一位工作人员在那里招工,我去的时候她看了一下我的身份证,说:“你超龄了几个月,应该也还行吧,先填表吧,加个微信,我回去跟领导确认一下,看看能不能让你进来。”然后我就回去等消息。等到我这个20岁的学生去应聘的时候,同样还是这个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表示说,“我看得你好顺眼,你直接来上班,体检完直接来上班。”我晚上回去又给这个工作人员发信息问有没有跟领导确认能不能进厂。她说:“领导说不行,你这个大了几个月,要不我把你推荐去隔壁的厂吧。”所以我是遭遇了年龄歧视的,但是这个歧视还好,还是给了我一点希望的。我没有进这家厂,我进了隔壁厂。但是在我跟学生进的第一家工厂的年龄限制放得更宽,只要40岁以下都可以进厂。
陈龙:您觉得把田野做好的话需要关注什么,或者有没有一些好的做田野的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
许怡:可能大家听到我进流水线打工觉得是比较有趣的经历,但是进工厂当流水线工人还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我是被固定在那个工位上的,我首先要完成我手头上的工作,然后才可以利用一些工休的时间或者吃午饭这种休息时间跑去看我关注的机器换人的现象、机器跟工人之间是怎么互动的,所以时间上会非常紧凑。我也不能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去跟工人互动和交流,不能提一些太复杂的问题。
但是也确实看到很多真实的现象,举一个例子,我去的第一家工厂有一个岗位叫自动化操作员,上面招工的条件写着说有培训,还有岗位补贴。大家一听“自动化操作员”岗位名称觉得好像也不错,至少比流水线工人听起来是更高端的岗位,但是只有我进去工厂以后才发现,他们具体干的活其实就是给机器做一些打下手的工作,简单的组装,把工件摆上去,机器弄好再把它卸下来,就是很简单的活。这样一个现象,如果我不进到工厂的话,我可能会以为引进机器人之后,工人的技能和各方面的工作条件都有提升,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我还有第三段田野经历,同样也是进工厂,但是这次进厂得到管理层的同意和许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可以观察到的东西、可以了解到的东西丰富得多,因为我可以自由地出入车间,还可以比较自由地跟工人进行交谈。在跟工人交谈的过程中我得到很多工人正面的反馈,最重要的是我没有把他们当作索取访谈资料的对象或者工具,我是把他们当作一个个值得尊重的个体去聆听他们的经历,他们会说很多跟我关注的主题无关的事情,比如有的女工会跟我说儿子和儿媳妇闹什么矛盾,又或者是自己的孩子在学校表现不好等等。他们也是很缺乏愿意去关心和聆听他们故事的人,我作为一个研究者,我去听他们讲述的过程中,也可以给到他们一些同理心和正向的反馈,这样一个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是良性的。
陈龙:我们都知道做社会学研究,田野十分重要,沈原老师您做田野这么多年,在您看来什么样的田野是好的田野?或者说成功的田野?
沈原:现在有一些教科书列了一些标准,美国社会学家提到你的田野资料要有可感知性,你的调查要有异质性,你要能够及时跟进等等这些标准。就我个人认为,我觉得做田野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调查。现在社会学里很多研究做的时间太短,大家有很强烈的直接的功利目的,我做这个田野就是要出个paper,我为什么要写这个paper?是因为我找到了一个有趣的概念。因果已经倒过来了,其实田野需要你非常长期地做。当然我们在当代社会做田野,长期扎根在工厂里面有它的不可能性,但是许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就是你可以通过在一个点上多次进入的办法。我想,所有的工厂和社会单位,可能最不喜欢的就是社会学家,一进来看这看那,问这问那,到各种地方去找材料,人家不愿意让你知道的东西都要拿走。那怎么办?我觉得就是坚持介入,你要想办法,一次待的时间可能不太长,你多次进入,能有一定的弥补。
陈龙:这本书里提到一个核心概念叫“机器霸权”,我想问许老师最开始是怎么想到这样一个概念的,这个概念是怎么提出来的?
许怡:其实这个概念之所以会在脑海中冒出,最开始是受到很多前辈劳工社会学家的启发,包括沈原老师早些年提出的“关系霸权”,还有布洛维教授提到的“霸权政体”。结合我自己的田野经验,我在田野中看到一些原本没有预料到的现象:工人明明在生产过程中发现这些机器有问题,但他们为什么还是会默默地接受,甚至有些人可能假装看不见这些问题,又或者说他局限于自己特定的工作岗位,没有看到整个生产的流程,所以他也看不出机器做得好不好。也有一些工人看到这些问题,也采取一些积极的做法,比如他直接关掉机器,就用人工操作,去生产,做得也不比机器慢,但最后他们也不得不臣服于管理者的权威。我书中写到一个例子,一个分拣工站的工人,他们把机器停了,高层管理者跑来说,“你们这些人懂不懂得科学的办法?你们用这些土办法来解决问题。”他把工人的做法——尽管对整个生产节奏、生产进度完全没有负面影响——比喻成是非常土的办法,使用机器的办法才是科学的办法,这个就在知识层面上、认知层面上,把工人给贬低了。
我发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其实机器霸权是有几方面的体现:一方面是在观念上面对工人进行统识,让工人觉得他们做的不如机器好,这种统识既来自内部工厂管理的方式,也来自外部。有很多媒体报道一直宣扬机器就是做得快、很稳定,而人工作会有情绪,累的时候就会做得比较慢等等。另外一方面是在生产过程中各种设置,来强化机器对工人的支配。比如刚刚我介绍的这个例子,在结束了他们那段小冲突之后,管理人员做了一件事,他在工站上面加装了一个指示牌,上面写着“禁止随意关开机”,就是工人不能擅自动这个机器,你有什么事情只能找组长处理,他通过这样一系列做法,既有观念上的统识,也带有强制性的操作,把这样一套机器霸权在工厂里面建立起来。
沈原:在现代的工厂里面,一定是管理者支配工人,都是支配。其实支配有两个方式,一个方式是强力,靠力量去支配,你到工厂里会发现贴着很多标语,“违者罚款”“违纪开除”,这些都是力量,等于是暴力的支配。但是更巧妙的一种支配是他说服你,他哄着你去干活,他表面上看着和你是很亲密的兄弟,但是他用这种办法,靠说服力来让你干活,甚至让你参与对自己的管理,甚至剥削,这是一种精致的支配,这叫霸权,这是从葛兰西这支流传下来的概念,它和暴力的支配正好是对立的。
机器为什么能形成霸权?其实它本身代表着一套意识形态,而这套意识形态在社会里头形成多年,运行多年,机器代表科学,科学技术就是先进的,先进的就是对的,就是我们要服从的。我没有做好,问题出在我自己,是因为我违背了科学。工人为什么接受这一套?明显地看到机器要占位了,要把我赶走了,我为什么还认为它是对的?这个意识形态怎么做一个区分。许怡老师的理论贡献主要是在这个方面。
许怡:沈老师这番总结非常深刻,我还想在沈老师基础上再稍微补充几句。在书中我们更多地看到工人对机器的态度有两种,一种是没有意识到机器霸权、机器神话,另一种虽然好像意识到了,但是也无力作出改变。这两种情况听起来还是有一些悲观的,让我们看不到改变的希望在哪里。我想这不是工人的过错,而是我们还缺乏一种工人之间的团结机制,让他们没有机会就彼此的发现、观察去进行交流互动,并且以更集体化的方式去予以反应,工会在这里面也没有充分发挥它的角色。
陈龙:我不知道许老师在制造业工厂当中做田野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老板管着机器,机器管着工人,如果是这样一种秩序结构的话,您提的机器霸权这个概念,有没有可能从制造业延伸到服务行业,甚至延伸到在座的每一位?另外,如果工厂的这套等级秩序,老板管着机器,机器管着工人,这样一套等级秩序存在,而且还在蔓延的话,您觉得未来的社会有没有可能三大等级,富人在上面,机器在中间,很多穷人在下面,这样的等级从工厂延续到整个社会,会有这种趋势的感觉和判断吗?
许怡:我早些年做研究的时候还是觉得工厂工人这一类工作,跟脑力劳动者和白领的工作有很大的差异,差异就在于工厂的生产过程、劳动过程是非常直观可见的,你有没有在偷懒、怠工,管理者一眼就可以看见,但如果是白领劳动者,在电脑前工作,老板也不会时时刻刻在后面盯着你,你是在摸鱼还是在认真工作,其实老板没有那么容易进行监控。但是近几年发现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对脑力劳动者的监控越来越成为可能,比如有些公司会给员工的电脑安装上一些监控软件,还有摄像头,导致上班摸鱼也变得越来越难。所以这样一种对劳动过程的监控,肯定是从工厂蔓延到各行各业。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自治学派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社会工厂”,它的意思是指工厂这样一套管理的模式会蔓延到整个社会不同的行业里面。
关于你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会出现的景象。但是机器没有生命,我觉得不太适宜把机器放进三大阶层的划分里,可能就是两极分化了,一端是最顶层的掌握机器、掌握大数据等数字资本和科技资本的超级富豪,另外一端就是最底层的这些人。中产有可能没落,因为中产所具有的高技能也会随着像AI技术的普及而慢慢失去它的市场价值。不过回到我们自己的职业身份,作为社会学者我们主要还是做经验研究,所以我们很难对没有发生的事情进行预判,只是说存在这样一个可能。
另外,我还是比较相信社会建构论这一套,技术是不是必然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发展?这一点应该由整个社会的相关利益群体共同决定,包括在场的你、我、他,我们都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我们应该有权利参与讨论技术该往哪个方向发展,是往不断把人类劳动力替代的方向?还是往一个更加多元的、更民主的技术方向发展?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陈龙:接下来我想聊聊许老师这本书的写作,您觉得什么样的写作或者您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触及到大众,您的写作方式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写作方式背后的初衷是什么。
许怡:出版这样一本半通俗半学术的作品,也是迫不得已,因为拿不到学术出版经费的资助,刚好广西师大出版社这边给了我一个出版的机会,也让我有机会把本来是偏学术的作品写得相对通俗化。
陈龙:说到写作,我也想问沈原老师关于写作尤其是劳工作品的写作,您对于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有什么样的期许,我们该怎么写好的劳工作品?
沈原:从劳工社会学来说,首先你能提一个好的经验问题,它得是个问题。不光是你自己在那喋喋不休,而是读者看起来,我怎么没看出来这是一个问题。这是我们讲的经验的困惑。我们是社会学,我们不仅仅是新闻学,我们不仅要提一个好的问题,要讲一个好故事,我们还得说清楚这个道理。当年我和郑也夫他们编三校(清华、北大、人大)社会学论文集的时候,我给大家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讲个故事,说个理儿,你提出这个问题后面告诉我一个社会学的道理,所以问题的经验困惑后面一定有一个理论的困惑,把这两个困惑加在一起,用它来引导整个文章,那一定会是好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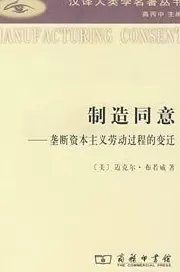
举个例子,布洛维的博士研究,一开始还没完全计划好要做工厂民族志。他当时没拿到芝加哥的博士论文奖学金,他得找一个活干,得先养活他自己,他进了工厂。他一到工厂里头就发现,工厂车间里的工人并不像当时流行的布雷弗曼所说的,工人是被动的,是机器的附庸。他进到工厂一看,工人在热火朝天地从事资本主义的劳动竞赛。他后来写了一段很有名的话:“当我下班以后回到自己住的小屋里,我捧着那个嗡嗡作响的脑袋,我才能够问自己,我干吗要这么努力地干活?我为什么把自己变成剥削自己的帮凶?”工厂对工人来说,工厂不是你的,劳动过程不由你管,产品你也沾不上边,那你干吗这么玩命干活?这是他的经验困惑。他提出的理论困惑,就是“同意”,工人这么努力地干活,其实就是认可资本主义的车间秩序,那是一种同意,这个同意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所以他的《制造同意》这本书,是把经验困惑和理论困惑放在一起引导了全书的形成。
所以我觉得一个不光是劳工社会学的文章,所有社会学的文章,一定有一个好的问题,而好的问题分成经验困惑和理论困惑两个层面。再退一步来说,也许你一时提不出来理论困惑,但是你至少有一个经验困惑来引导你的文章,让别人能够读下去。现在我们大学里面基本把写论文变成中学老师的命题作文,绞尽脑汁的去编一个问题,那样的问题打动不了作者,也形成不了好的文章。







还木有评论哦,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