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举行的荷兰大选初步结果已经出炉。共有多达27个政党、1166名候选人参加此次选举。
根据荷兰广播联盟(NOS)于当地时间10月30日晚11点公布的实时数据,中间派政党六六民主党(D66)在荷兰国会第二院(即国会下议院)的席位预计将有明显增长,与当前最大党——极右翼的荷兰自由党(PVV)席位将会持平。然而,这一变化并不能简单解读为荷兰政治右转后的“向左回摆”。极右翼各政党的影响力依旧强劲,而新一届政府的组阁进程仍需时日才能尘埃落定。
荷兰政党政治的高度碎片化,是当代欧洲议会民主制的一面镜像。荷兰选民当前关注的住房、移民等议题,虽然具有鲜明的本地语境,却同样折射出欧美发达国家在社会结构性危机中所面临的共同困境。
多党共治模式在社会极化与信任危机下的疲态
本次荷兰大选之所以提前举行,其直接背景是由迪克·斯霍夫(Dick Schoof)领导的联合政府在2025年夏季倒台。该政府于2024年7月正式成立,由极右翼的自由党、右翼的自由民主人民党(VVD)、中右翼的新社会契约党(NSC)与农业民粹主义的农民公民运动(BBB)四党组成。
尽管在2023年大选后,自由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其党首赫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的民族主义、反移民与反穆斯林的极端立场使得其他政党拒绝接受其出任首相。四党联合政府最终同意由具有安全与情报部门背景的公务员、前司法与安全部秘书长的迪克·斯霍夫担任首相。尽管四党政治立场均属右翼,但在移民、财政预算以及巴以冲突等多个问题上持续爆发尖锐分歧。

荷兰莱顿中央火车站门口的政党宣传牌。本文图片均为笔者拍摄
2025年春,斯霍夫政府在庇护、家庭团聚与居留许可改革问题上爆发激烈冲突。自由党要求几乎全面冻结庇护申请、限制家庭团聚,并主张退出欧盟的移民机制。而现任北约秘书长吕特(Mark Rutte)之前长期领导的自由民主人民党虽然支持收紧庇护政策,但仍希望保留欧盟框架内的协调,以维护荷兰的国际信誉。农民公民运动与新社会契约党也主张限制移民,但前者更关注地方承载力与区域安置问题,后者则坚持法治与国际公约原则,拒绝采取极端措施。截至2025年3月,荷兰民众对斯霍夫政府的信任度已降至16%,四党联盟未能兑现其在住房、移民及社会安全方面的选前承诺,成为选民普遍不满的焦点。
2025年6月,自由党提出新的庇护上限方案,要求立即实施配额和关闭部分收容中心。新社会契约党认为此举违法荷兰宪法与欧盟法律,因而拒绝签署。6月3日,自由党党首维尔德斯宣布撤回对内阁的支持,首相斯霍夫随即向荷兰国王亚历山大·威廉递交辞呈,斯霍夫政府正式倒台并转为看守状态。
然而,荷兰政局在8月迎来第二轮危机,8月22日,新社会契约党所属的三位部长集体退出斯霍夫政府,指责斯霍夫政府在移民、执法与新闻自由等关键议题上绕过内阁程序决策,缺乏依法行政的自制力。此后,政府行政几乎陷入停摆。斯霍夫政府的崩溃不仅源于政策分歧,更折射出荷兰多党共治模式在社会极化与信任危机下的制度性疲态。
多党选后席位剧烈变化,但政治版图并未重组
截至当地时间10月30日晚上11时,在开票率99.7%的情况下,根据荷兰广播联盟与荷兰通讯社的选举数据计算:极右翼的自由党将从原先的37席降至26席,中间派的民主六六党则从9席跃升至26席,两党并列成为第二院最大党。前首相吕特所属的自由民主人民党减少2席至22席,左翼的绿色左派-工党联盟从25席降至20席,中右翼的基督教民主呼吁从5席大幅上升至18席。极右翼的正确答案2021党获得9席,民主论坛(FvD)取得7席,农民公民运动降至4席,而中右翼的新社会契约党则从20席一举跌至零席。
此次选举结果表明,自由民主人民党、新社会契约党与农民公民运动这三个右翼政党,因曾参与由自由党主导的斯霍夫政府而在选举中遭受明显损失。选民普遍认为这些政党在政府中未能发挥积极作用,斯霍夫内阁也未能兑现选前承诺,实现强有力决策与有效施政的目标。
然而,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荷兰政治正“恢复常态”。即便自由党席位显著下降,若将第二院内的极右翼与农业民粹主义政党席位合并计算:包括自由党、正确答案2021党、民主论坛与农民公民运动四党,其总席位仍达46席,与上届议会的48席几乎持平。这意味着,自由党与农民公民运动丢失的席位很大程度上被其他极右翼政党所吸收,极右翼阵营的总体力量并未削弱。
同理,自由民主人民党与新社会契约党等右翼、中右翼政党流失的选票,主要转向民主六六党与基督教民主呼吁。民主六六党领导人罗布·耶滕(Rob Jetten)在此前电视辩论中的表现也为该党得票增幅较大有所助益。
表面上看,多个政党在选举前后席位变化剧烈,似乎呈现政治版图重组的景象,但从整体结构看,这更多是荷兰政党体系高度碎片化的反映。各主要意识形态阵营的议席总数并无显著变动。换言之,荷兰政治的基本格局依旧稳定,并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结构型转向。
荷兰政坛上,包括此前加入自由党主导政府的自由民主人民党在内的多个政党,都已明确表示选后不会参与由自由党领导的极右翼内阁。因而,未来要在第二院150席中凑足76席多数、组建执政联盟,将极为艰难。

莱顿街头的民主六六党广告
当前较具可行性的方案,是由中间派的民主六六党牵头,联合基督教民主呼吁、自由民主人民党等中右翼、右翼政党组成政府。然而,仅凭三到四个政党恐难实现多数支持,组阁可能需四到五党协商完成。这种多党联合在短期内难以改变荷兰决策过程多方掣肘、效率低下的结构性问题,政策推进速度恐将延续斯霍夫政府时期的缓慢节奏。
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由中间派的民主六六党与左翼的绿色左派-工党联盟牵头,联合部分中间偏右及中间偏左政党组成中间政府。无论最终形态如何,新政府在选民最为关注的住房、农业、气候与科技领域都难以形成完全共识。在移民议题上,虽然分歧尚在,却较有可能形成一定的公约数。
移民、气候、科技,荷兰的问题也是其他欧洲国家的通病
在此次荷兰大选投票日前,选民最为关注的议题包括住房、移民、气候、农业、医疗与科技。总体而言,荷兰选民关注的议题以国内事务为主,呈现出明显的“市政化”倾向。但这些议题在更广泛的欧洲背景下亦具有代表性,反映出当代社会福利国家与议会民主制度结合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发达国家中普遍面临的困境。
荷兰选民关注的首要议题是住房问题,也是具有荷兰特色的发达国家生活成本危机问题。自二战以来,荷兰社会长期受到住房供应紧张与市场失衡的困扰,甚至在1981年因房屋短缺曾引发大规模骚乱。到了2025年,住房供应的紧张程度已达到战后最高水平。根据荷兰中央统计局(CBS)数据,2024年全国住房缺口约为40万套。
荷兰土地稀缺、空间规划极为细密。根据荷兰《环境法》(Omgevingswet)规定,住房建设项目的审批虽然名义上集中于市政层级,但仍需协调中央与省级规划目标,并评估洪水安全线、农业保护区、自然保护区与社区邻避问题(NIMBY)等因素。此外,荷兰国土面积仅约4.1万平方公里,而北部地区如格罗宁根省存在土地沉降,不适合大规模住房建设,大片洪水缓冲区及自然湿地也被划入非开发区,绿地与农业用地受到严格保护,可用于住房开发的土地实际非常有限。在本次选举中,几乎没有政党在选举纲领中提出改变这些结构性约束。
在大选前的政党辩论中,争议最明显的住房议题之一是是否取消住房贷款利息抵税政策。在对策上,绿色左派-工党联盟主张彻底取消房贷利息减免,以抑制投机并强化公共住房供给,基督教民主呼吁等中右翼政党支持渐进式改革,而右翼与极右翼的自由民主人民党、自由党则主张维持现行政策,并将住房紧张归咎于移民增长。即便左翼的政策得以实施,其影响也将是中长期的。如何在短期内缓解住房危机、安抚被排除在住房市场之外的年轻一代,缓解对于住房危机的不满转化为极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势能,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移民是与住房问题密切相关的、本次选举的另一核心议题。作为长期的净移民流入国,荷兰近年来因住房紧张和生活成本上升而出现明显的反移民情绪。这一趋势直接助推了2023年自由党的崛起与上台执政。斯霍夫政府执政期间实施的一系列移民限制措施,使移民流入速度明显放缓。在本次大选中,各党围绕是否继续遵守联合国人权公约和欧盟移民协定展开辩论,但分歧有限。从整体上看,荷兰政坛主要政党无论左中右都支持在不同程度上收紧移民与难民政策,分歧仅在幅度而非方向。
以荷兰为例,大部分中欧、北欧国家,尽管近几十年来一直是欧洲移民的净流入地区,但并未形成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文化。在移民身份上,“融入主流社会”的一元主义思维依旧占据上风。这种现象也反映了欧洲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身份焦虑。虽然当前欧美普遍出现反移民浪潮,部分缘于生活成本危机的社会经济压力,但从更深层次来看,欧洲民族国家历史上形成的排他性身份结构,都在潜移默化地强化着这种对民族认同的固执与防御。
紧随住房与移民之后,气候与农业问题成为本次荷兰大选中另一个密切关联的议题。荷兰以出口导向型立国,目前按农产品出口总值计算是世界第二大农业出口国,每年农产品出口收入高达约1200亿欧元。在面积有限、土地稀缺的滨海圩田之上,荷兰创造出如此高密度、高产出的农业体系,依赖的是高度集约化、“密植化”的温室种植与家禽工业化养殖模式,以及广泛使用化肥与农药的生产体系。这种高投入-高产出模式导致荷兰陷入严重的氮排放危机(stikstofcrisis)。全国河网水质长期在欧盟垫底,大量氮排放也推高了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与左翼政党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碳中和目标形成强烈对立。

海牙荷兰国会附近的农民公民运动广告牌
代表农民与小城镇选民的农民公民运动虽然在本次选举中仅维持约2%的支持率,但自2023年以来在斯霍夫政府中始终扮演关键少数角色,席位有限,却能影响所有涉及农业改革的议案,几乎使任何不利于农业现状的政策被搁置。而在2023年的荷兰国会第一院(上议院)选举中,农民公民运动得票率为20.66%,高居各政党第一,显示其在荷兰社会的代表性。农民公民运动的选民普遍认为,身处大城市的中间派与左翼政治力量对农村现实缺乏了解,一旦对大规模气候政策开绿灯,荷兰当前依赖出口的农业经济将难以为继。
右翼与极右翼政党,包括自由民主人民党与自由党,在这一议题上大体与农民公民运动立场一致,反对任何可能削弱农业产业的政策。可以说,在“以农为本”的荷兰,农业与气候议题的分歧几乎贯穿了整个政治光谱:从左翼的绿色左派-工党联盟,到中间派的民主六六党,再到中右翼的基督教民主呼吁以及右翼、极右翼政党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政策断层。
在这些议题中,健康问题主要涉及荷兰卫生保健体系的系统性压力与费用持续上涨,医护人员严重短缺。根据荷兰公共卫生、福利及体育部预测,到2035年全国医护人员缺口将达到约26.6万人。然而,在短期内,由于政府财政持续紧缩,各政党普遍承认这一问题难以得到根本缓解或改善。医疗体系的压力是选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最直接、最切身的议题之一。它不仅反映了荷兰公共部门在财政约束下的治理困境,也折射出发达福利国家在老龄化社会中普遍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在科技政策方面,荷兰政坛从左翼到右翼的大部分政党形成了罕见的共识:政府应当强化对科技企业发展的监管与战略主导作用,普遍认为荷兰不应继续放任美国与中国大型科技公司的影响,应加强对欧洲自主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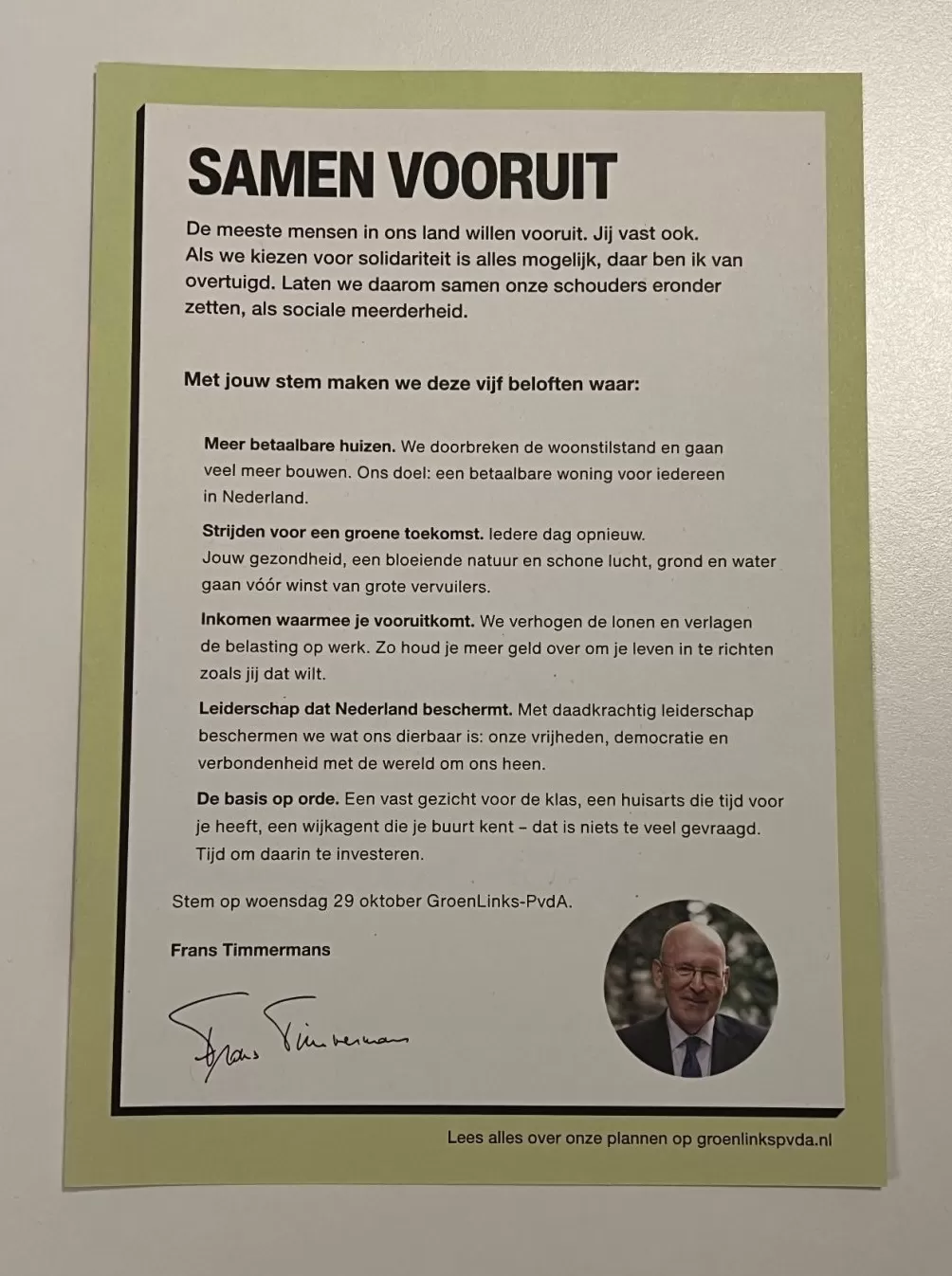
绿色左派-工党联盟竞选宣传传单
这种对大型科技企业的普遍怀疑主义倾向,一方面体现出欧洲国家在中美科技创新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对自身技术竞争力、创新力的落后焦虑。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欧洲社会主流对于数字化转型的复杂情绪,在缺乏对科技创新具体内容的深入理解时,往往转向一种对外部科技力量的防御性不信任的集体心理。
新政府“公约数”有限、难推有魄力的改革
综上所述,此次荷兰大选中,选民最为关注的议题——无论是住房、移民还是医疗健康,在更深层面上都折射出,以荷兰为代表的欧洲发达国家在生活成本危机背景下,国内政治关注重心发生的普遍特质。选举之后,虽然最有可能形成一个中间派或中右翼的联合政府,但除了移民与科技这两个政策领域以外,各潜在执政党派在其他关键领域的立场差距依然明显。由此可预期,新政府在农业、气候与住房等问题上的施政空间将十分有限,而在公共债务持续面临上升压力,财政赤字将逼近欧盟赤字上限的条件下,公共卫生与社会福利领域也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可预见的未来,移民政策仍将是荷兰政府短期见效快,宣示效应强的政策领域。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政党,尽管具体主张存在差异,但在总体方向上已形成一定的共识。即便如民主六六党作为仍保持一定全球主义倾向的中间政党领导组阁,也很可能在未来的联合政府中无法反对进一步收紧移民与庇护政策的多数声音。科技政策的情形亦然。左、中、右各派在强化国家对数字科技的监管与限制中美大型科技企业影响方面高度趋同,这将成为新政府少数能够达成政策共识的领域之一。
然而,荷兰议会民主制的高度碎片化,决定了任何可能成功的组阁方案都需要包含数个政治立场相异、政策路线相左政党共同参与。在这种条件下,联合政府往往只能在少数“公约数”上达成共识,但缺乏改革魄力的执政方式。
从这一意义上看,荷兰的政治格局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某种欧洲国家普遍面临的境况。
荷兰的组阁过程预计仍将旷日持久,但其政策走向与政治重心的大致轮廓,已经在此次大选结果中显现。
(曹茗然,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博士候选人)






还木有评论哦,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