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有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洗冤录”系列,藉由历朝历代的真实案件,窥古代社会之一隅。
有女名失林
黑水城,一座被风沙掩埋之城。千年之前这里还是一个绿洲城市,在这个丝路中转要地,曾发生了一桩情节跌宕起伏的婚外恋案。
故事的女主角叫失林,案发时年仅二十四岁。失林是大都人氏,似乎姓张,从破碎的残存文书看,张二似乎是她父亲的名字,母亲名为春花,但失林的所有档案中都没有称自己为张失林。失林的名字,据说是常见的波斯名“Shīrīn”的音译,但考虑到失林生活的年代已经是元朝接近撤离中原的至正二十二年(1362),因此很难从名字判断出失林到底属于色目人还是汉人,抑或为色目人、汉人的混血后代。这一点,也许对别人来说并不重要,但在接下来失林要面对的指控中却极为重要。
失林虽然是京籍人氏,但这层“根脚”身份显然没能给她带来更多利益。她的家境比较贫困,她的父母在媒人倒剌大姐的撮合下,将她“过继”给一个回回商人脱黑帖木作为养女,虽然美其名曰过继,实际上就是把失林卖给了这个回回商人。
脱黑帖木出现在大都,是因为做生意。他似乎奔波于丝绸之路上,正打算将大都的物货分做两批,一批运送到岭北行省,另一批则继续跟着他回到西域。至于他为什么要收养失林,我们已经无从得知,或许是因为这名在丝路上纵横捭阖的商人需要一个能够用心服侍他、替他打理家业的人。
失林并非好的人选。对于父母的选择,失林并无抗争的权力,但在内心深处,她对自己被贩卖给丝路商人做养女的事情是抗拒的。因此,尽管她与脱黑帖木一路来到了黑水城,但此后她拒绝继续与脱黑帖木向西远行。按照她的供词所称,一路上她非常害怕脱黑帖木压良为驱,把这位养女彻底变成自己的奴婢。如果继续往西行,就会离开元朝实际控制的领土,元朝的法律无法再为她提供任何保护。
商人觉得自己的时间是宝贵的,脱黑帖木甚至不愿多花一秒去哄哄这个养女。他决定就地卖掉这位买来的养女,以最大限度收回自己的本金。这时候,阿兀出现了。阿兀是黑水城原住民,三十岁,是个虔诚的答失蛮(穆斯林),归当地礼拜寺奥丁哈的大师管辖。阿兀也是商人,与脱黑帖木一样,有时候会往岭北行省或西域倒卖物货。户计上,阿兀属于纳包银户,因此他拥有娶妾以及豢养驱奴的能力。阿兀已经有妻室了,但他依然决定从脱黑帖木手中购买失林,求娶为妾。于是,阿兀写立了婚书,从脱黑帖木手中接走了失林。
风起黑水城
闫从亮如果没有来到黑水城,失林可能也就跟着阿兀安安稳稳地过下去了,尽管她的内心可能还有些许不甘,因为阿兀经常打骂他。闫从亮虽然是军户,理应按其户计属性服兵役,但他选择当逃兵。为了躲避战乱,他逃到黑水城成为流民。应知失林案发生时,各地红巾起义此起彼伏,中原大地已经是“卷起农奴戟”的星火燎原之势。闫从亮原来住在陕西巩昌,至正十九年(1359)时,红巾军攻破了巩昌城,闫从亮被迫逃亡。他先一路北上逃到甘州,随后又于至正二十一年(1361)逃到了黑水城。
留意过元朝普通人姓名的人应该能意识到,闫从亮的原生家境应该尚可。在《元典章》大量的案例中,普通人的姓名要么是阿猫、阿狗、驴儿等花名,要么是千三、小六、十一等序齿代称,要么是歪头等暗示某些身体特征的损称,鲜有像样的名字,闫从亮显然不属于上述情况。黑水城与内地州府不同,地处西北,早期作为西夏的军事重镇,到了元朝则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商业城市。闫从亮离开原生家境,逃到黑水城后,生活似乎相对拮据。在认识失林前的近两年的时间里,闫从亮一直跟随城里人沈坊正制作油皮韂度日。
某天,闫从亮正在沈坊正房顶晾晒油皮韂时,有不认识的人跑来请闫从亮去阿兀家帮忙从井里打水。就这样,闫从亮认识了失林。自此之后,闫从亮经常去阿兀家帮忙打水,时常与失林相见说话,终于干柴烈火地好上了。
一来二去,失林萌生了跟阿兀离婚,嫁给闫从亮的想法。但她心里很清楚,阿兀娶她为妾,怎么可能轻易将她放走?于是她就开始与闫从亮合计,想要找出一个可以长相厮守的办法。对于闫从亮来说,带着失林私奔,实际上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当时天下大乱,闫从亮如果带着失林逃到红巾军,甚至逃到朱元璋的地盘,元朝的亦集乃路总管府就无法对他实施法律上的“长臂管辖”。
但闫从亮没有这么做。作为一个极具“契约精神”的人,闫从亮坚持要在元朝的法律框架内做文章。很快,他就打起了失林婚书的主意。元朝法律规定,凡结婚,不管是娶妻还是娶妾,都需要写立婚书作为结婚证明,婚书的内容必须包括男女双方家境、身份以及许诺的聘财、嫁妆,约定的婚期等内容,不得使用朦胧语句搪塞,且须由男女双方家长、媒人、担保牙人签字画押确认。为了防止伪造婚书,元朝还要求应在婚书背面中间写下“合同”二字,然后将婚书分为两半,男女双方各收执一份,作为日后不履行婚约的告官凭证。今天契约多称为“合同”,或许就是从这个时期慢慢演化而来。
于是,在一次约会中,闫从亮撺掇失林趁着阿兀不在家的时候,将婚书搜出来付之一炬。失林听进去了,恰好这段时间阿兀到岭北去做生意,不在家,失林得以在家好好搜检她的婚书。但失林不认字,只能按照闫从亮所描述的婚书的样子搜寻,最后从阿兀的红匣子中找到了三份疑似婚书的契约。
失林将这些契约带给了闫从亮,嘱咐他辨认一下哪一份才是她的婚书。闫从亮可能有一些文化,能够辨认出这些契约是汉文的契约,但具体写什么,他似乎也看不懂。这时,邻居徐明善正好路过礼拜寺,闫从亮便请他帮忙辨认这几份契约。徐明善是读书人,一下就指认出失林的婚书,另外两份则分别是阿兀购买两个驱奴木八剌和倒剌的契约。
闫从亮又跑到史外郎家里,谎称自己在东关捡柴时捡到了这几份契约,请史外郎辨认一下文字上写的是什么内容。史外郎的原名叫史帖木儿,僧人户计,称他“外郎”,大概是因为他在当地亦集乃路总管府做员外郎的官。史外郎毕竟是官员,文书经验丰富,他一眼就看出了这些被“丢弃”的契约不是废纸,而是阿兀的贵重信物。史大官人看完后跟闫从亮说,其中一份是阿兀购买驱妇倒剌和驱奴答孩的契约,另一份则是失林的婚书。他嘱咐闫从亮,要随时将文书带在身上,不能毁弃,假如阿兀来找,要及时还给失主。彼时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贼喊捉贼的正是闫从亮。
经由徐明善和史外郎确认无误后,闫从亮很高兴,回去就与失林谋划,打算第二天找个机会把失林的婚书烧毁。但失林已经等不到第二天,两人于当天傍晚上灯时分,在闫从亮家借机用灶窟将其中失林的婚书焚毁。剩下的两份契约则重新交由失林收回。
闫从亮的思路是,只要没了婚书,阿兀与失林的婚姻关系就处于可争议状态。根据《元典章》中婚姻断例的记载,元朝官方曾规定,如果没有婚书,或婚书中用词朦胧,没有在婚书背面写下“合同”等字,争告到官时,官府将视之为“假伪”,婚姻效力很可能据此宣布无效。看得出来,闫从亮是“懂法”的,他想利用这一点消除阿兀与失林婚姻关系最强有力的证据。烧毁婚书后,闫从亮嘱咐失林在一两天后去官府告冤,称被阿兀强娶为妾,婚后阿兀更是压良为驱,要把这个娶回家的妾迫害成贱民身份的驱奴。这样,根据以往的司法经验,官府大概率就会断令阿兀与失林离异或者婚姻无效,并要求阿兀放良。一旦这些都得到实现,闫从亮即决定“做宴会”明媒正娶失林,“永远做夫妻”。
半路生变故
史外郎不是“屎壳郎”,但对于闫从亮来说,他是根妥妥的“搅屎棍”。如果不是他的“告密”,上述闫从亮的“奸计”可能就得逞了。史外郎大概与阿兀是有交情的,毕竟对于本地有头有脸的商人,地方官员应该多少有些来往。阿兀什么时候从岭北回来已经难以知晓,但应在案发前后,他就已经回到黑水城了。大概在替闫从亮辨认文书后不久(供词上写闫从亮是十一月二十七日烧毁文书,史外郎在二十九日就见到了阿兀),史外郎就在街上碰到了正在忙活的阿兀(可能是有意去找阿兀)。史外郎告知阿兀,自己刚刚从闫从亮那里看到了几份契约,上面有阿兀的名字,为此他建议阿兀赶紧回家查看一下自己的契约是否真的丢失。
因为史外郎的出现,真相就此浮出水面。阿兀回到家,果然发现自己红匣子里的契约都不见了。阿兀开始在家里盘查,最终将作案嫌疑锁定在了失林身上。考虑到阿兀经常在家打骂失林,不排除他用家暴手段从失林嘴里套出缘由的可能。总之,从供词上看,失林最后承认了是她将三份文书拿给闫从亮看,最后闫从亮退回了其中两份,插放在铺盖中。阿兀不但从失林嘴里获得口供,而且还从邻居徐明善那里得到证实。徐明善供出了闫从亮,阿兀又顺藤摸瓜从失林嘴里得知了她和闫从亮的计谋。
于是,阿兀决定到亦集乃路总管府起诉失林和闫从亮。官府迅速开审此案,所有的词状都在十二月内完成具结。现存词状虽然残缺不全,但阿兀、闫从亮、徐明善、失林、史外郎的词状都多少得到保留。阿兀是告状人,他在词状中写明了史外郎向他告知失林与闫从亮偷递婚书一事,请求总府予以主持公道,并列明失林和闫从亮为共同被告人,以史外郎和徐明善为证人。
确认了阿兀的诉讼请求后,亦集乃路总管府即派祗候李哈剌章带人去将被告人及证人徐明善押到官府。差去公干的李哈剌章,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属于承管人角色,负责案件具体操办事宜,包括即时约束好原告、被告、证人等,确保整个诉讼流程畅通。承管人在承办案件之前,需要订立承管状,保证完成承办案件。
作为犯罪嫌疑人,闫从亮采取锁收收监,即在监狱中需要佩戴枷锁。失林是女子,根据元朝法律规定可以免去枷锁散收。史外郎虽为证人,但本人是朝廷命官,所以不适用根勾羁押证人的制度。这里有必要补充说明一下元朝的狱政。元朝的监狱并非服刑场所,监狱中既关押未审决的犯罪嫌疑人,也关押着已决但未行刑的犯人(如已判死刑,正等候秋后问斩的死刑犯),还会羁押证人及其他关键涉案人物。根勾羁押证人的做法在今天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谬,但那主要是对古代证人传唤能力不足的技术补充手段。试想,在通信技术和交通水平较为低下的古代,如果不提前将证人羁押在府署,那么很可能会出现需要请证人出庭作证时,官府到处联系不上证人,或因证人居住地远离府衙,传唤周期过长等尴尬情形,甚至不排除散居在外的证人与涉事人串供等,因此证人必须提前到署,住进监狱中。
同样身为证人,史外郎的证词相对简单,这不仅是因为他无法对案件深层部分做过多证明,也因为他的官员身份,本路总管府审案的法官不可能过度地去讯问他。徐明善则不同,尽管从证词残片看到,他的证词与其他人的说法一致,但为了防止他像电影《九品芝麻官》中目不识丁的阿福那样有作弊之嫌,阿兀还是亲手拿着一张汉文文书让他当庭识读,以证实徐明善确实有能力读懂汉文。
最终,失林对案情供认不讳。作为整个事件中最弱势、最没有权利处分自我的失林,她能做的也只有承认。但失林的判词显示,这个弱女子仍然在做最后一搏。在供词中,失林顺着压良为驱的思路,强调阿兀试图将本为良民的失林转卖为低贱的驱妇,理由是阿兀认为失林系汉人,“怎能与我作伴?”据此,失林获得了一种抗辩的理由,即根据伊斯兰教义,阿兀不得娶异教徒或不尊重其俗的女子为妾。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失林的婚姻就可以被认为自始至终是无效的。
从逻辑上讲,失林的抗辩极为高明。根据元朝中书省在至元八年(1271)制定的婚礼规则,如果是同“类”人之间出现婚姻纠纷,则各依其“类”的本俗法来处置。如非同“类”,则以男家为主。现在,阿兀是回回人,失林是汉人,属于非同“类”的情形,则其婚姻纠纷,要以阿兀的本俗法作为准据。阿兀的本俗法,至少在原则上是不允许他与非答失蛮结婚的。
无奈的结局
从最后的判决结果看,亦集乃路总管府显然没有采纳失林的主张,失林被处四十七下笞刑,仍然发付给阿兀收管。目前的文书残片已经无法看到阿兀如何回应失林的抗辩,但根据美国学者柏清韵的推测,由于失林无从证明其原来的汉人身份,而他的养父又是回回人脱黑帖木,那么,即便官府进行推论,也只能得出失林乃回回人养女的确切结论。如果这种收养关系意味着某种形式的皈依的话,那么失林嫁给阿兀也就顺理成章,并不违反教义了。
最后遗留的法律问题是闫从亮与失林的通奸问题。通奸的行为,在今天的法律中并不被作为一种刑事犯罪认定,更多只是在道德上受到谴责以及受到刑法以外法律的约束,如党纪党规的处理等。但在古代,通奸是一种犯罪行为,从《唐律》以降,一直被认定为奸罪的基本形态——和奸。元朝关于“和奸”的法律规定基本沿袭《唐律》与金朝《泰和律》的认定思路,和奸有夫妇人最终定刑为杖八十七下,奸夫奸妇同罪。
尽管现有文书无法看出对闫从亮的最终定罪是什么,但根据奸夫奸妇同罪的原则以及失林被判笞四十七下的结果看,二人显然没有因奸情而坐罪,甚至已有的文书中连指控奸情的文字都不存在。一种可能当然是两人虽然产生恋情,但确实没有存在通奸情节。不过,囿于古代科技水平限制,这一点实际上在官府审断中很难被证明或证伪。考虑到社会舆情以及对妇女社会名誉的潜在损害,古代法律通常只承认“于奸所捕获”等即时犯奸行为,而严格禁止事后指认奸情的做法。
也就是说,即便闫从亮与失林存在通奸行为,只要阿兀未能“捉奸在床”,他就不能指控二人的奸情,否则,根据“指奸坐罪”原则,阿兀反而要受到法律的惩罚,甚至会变相强化失林的抗辩效力。这样看来,阿兀也是“懂法”的。
从被亲生父母“过继”他人,到养父以嫁为卖,再到丈夫压良为驱,以及情人闫从亮的救助失败,失林的遭遇,是古代妇女不幸婚姻的一个缩影。更可悲的是,建立在男尊女卑基础上的元代法律并不能保障她的权益,失林唯一提出的抗辩理由几乎毫无悬念地遭到法官驳回。失林的遭遇也不会是个案,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妇女,终究只能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中步履蹒跚地前进,并试图以星星点点般微弱的呐喊唤醒沉睡的人性,直到光明的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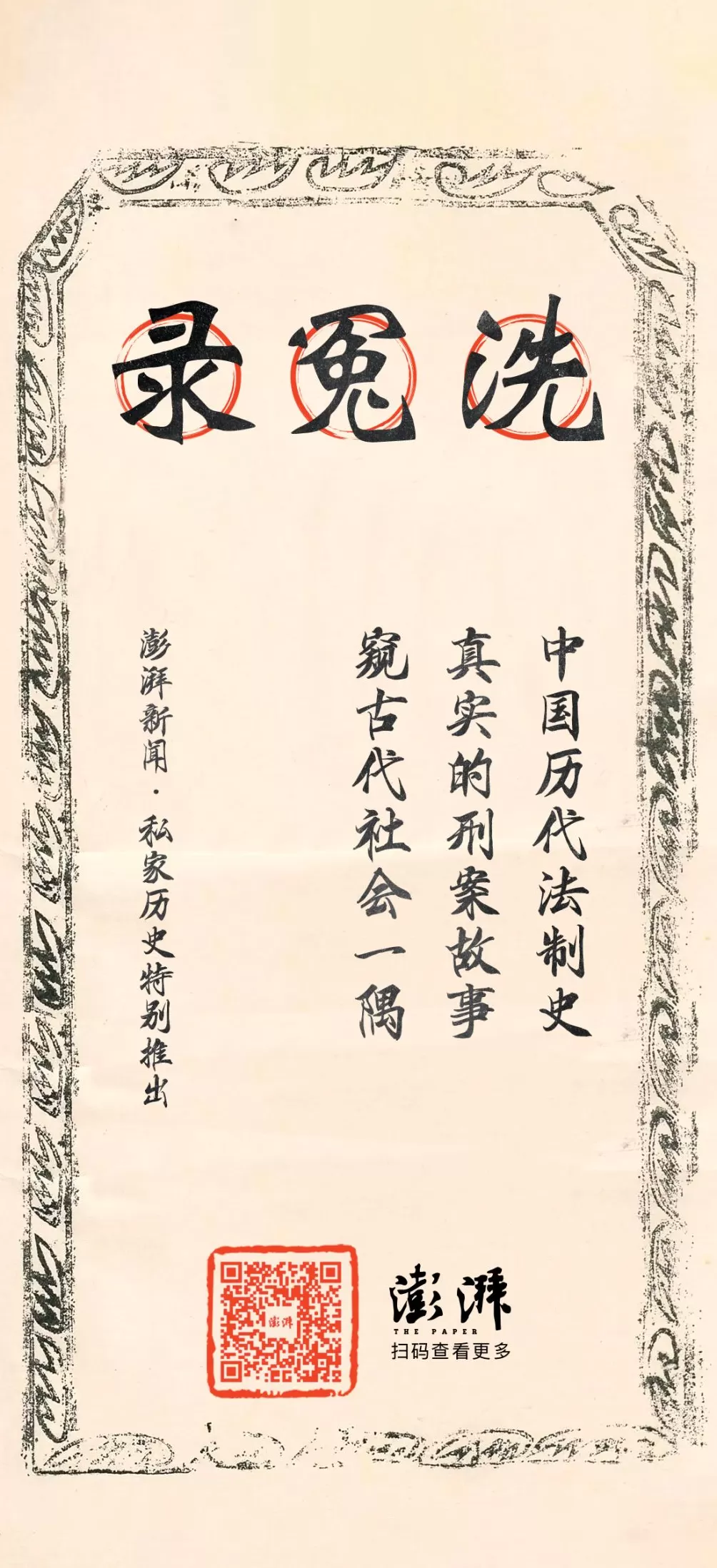







还木有评论哦,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