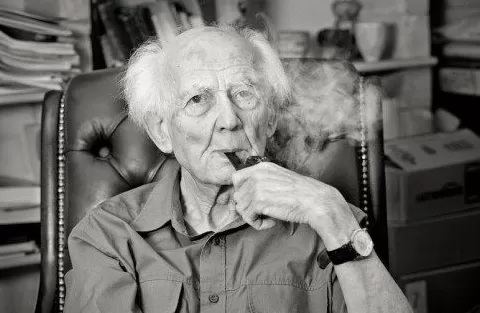
齐格蒙特·鲍曼
今天正值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诞辰百年,作为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当代社会思想家之一,鲍曼以“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这一概念精准命名了我们今天所处的生存境况——一切坚固的东西皆已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流动不居的关系、身份与价值。鲍曼的一生同样充满流动性,1925年生于波兰犹太家庭,二战期间逃亡苏联并投身军旅,后在华沙大学执教,又因政治动荡辗转以色列等地,1971年后定居英国,任利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直至退休,2017年在利兹的家中去世,享年九十一岁。
鲍曼不仅在不同地域和身份间不断迁徙,在思想疆域同样持续探索,一生著述颇丰,仅英文出版著作就达五十余部,内容横跨现代性批判、消费主义、全球化、社会不平等、个体身份焦虑、道德困境与暴力根源等诸多领域,而这些问题均围绕现代性的核心议题展开。鲍曼的写作深刻剖析现代文明的内在矛盾与人类生存困境,并始终贯穿着一位知识分子对个体道德责任的深切关怀。这份书单整理了鲍曼国内近五年翻译出版的著作,或可成为进入他思想世界的入口,透过文字重探他对现代生活的洞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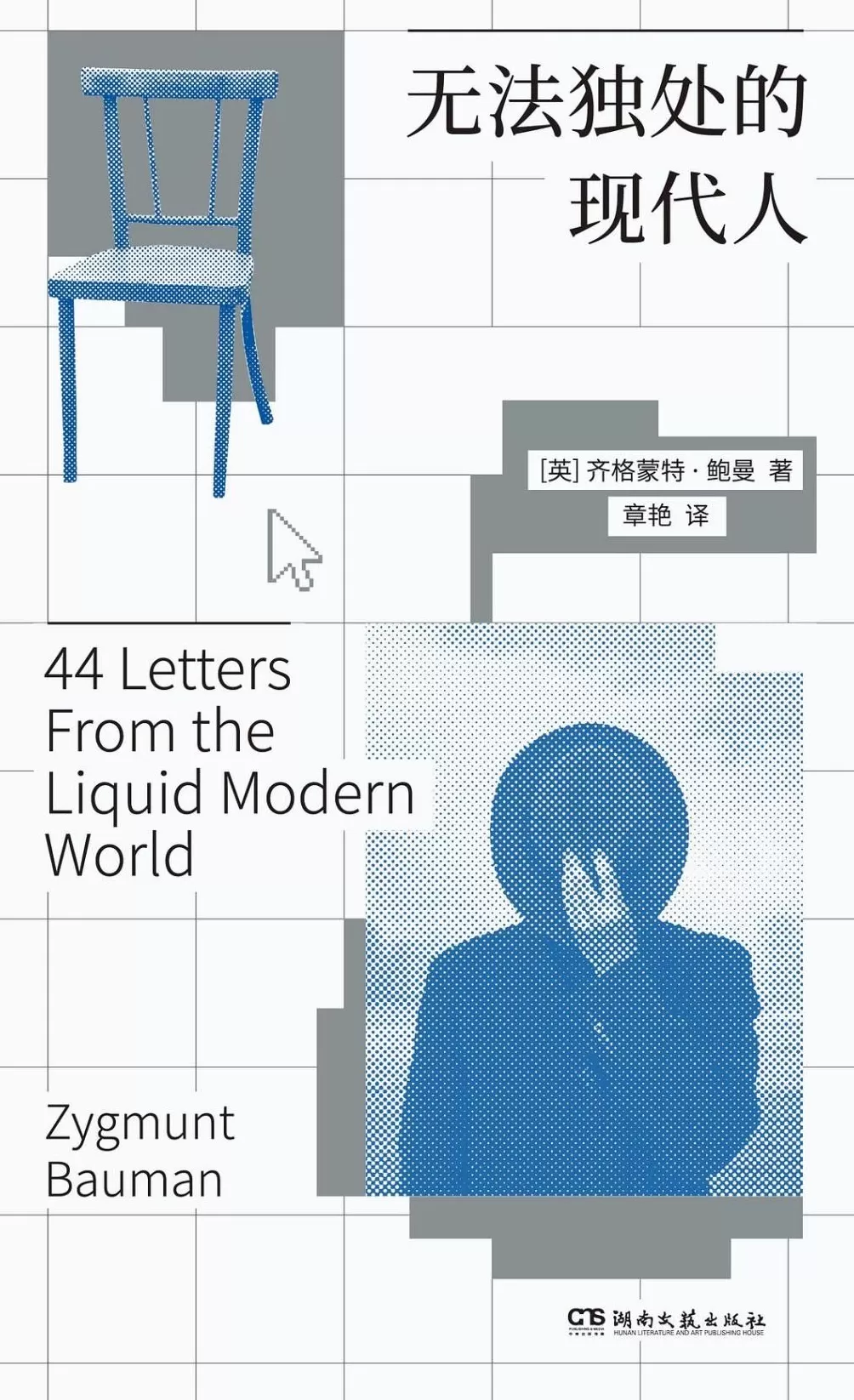
《无法独处的现代人》
章艳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中文首次翻译出版时间:2013年
原作名:44 Letters from the Liquid Modern World,2010年出版
“在逃离孤独的路上,你失去了独处的机会。独处是一种美妙的状态,可以让你整理思绪,去沉思,去反省,去创造。最终,赋予交流以意义和实质。可是,如果你从未尝过这种滋味,你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你放弃了什么,丢掉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真正重要的是自我定义和自我表达,愿意接受生活是一件艺术作品,而且必须是一件艺术作品。”
本书由鲍曼应《女性共和国》杂志编辑之邀,在2008年至2009年写的专栏书信结集而成。书中聚焦现代社会中人们所面临的焦虑与恐惧,记录并分析孤独、代际沟通、消费主义、知识焦虑等种种症候。在一个流动的现代世界里,不确定性消解了稳定的社会锚点,人们既害怕孤独又无法建立深度联结。鲍曼以审视的目光描绘出这个“液态”世界的图景,但并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而是让读者在以此展开的空间里进行理解和思考,从“永远在线”的状态中抽离,在独处中寻找应对不确定性和意义匮乏的内在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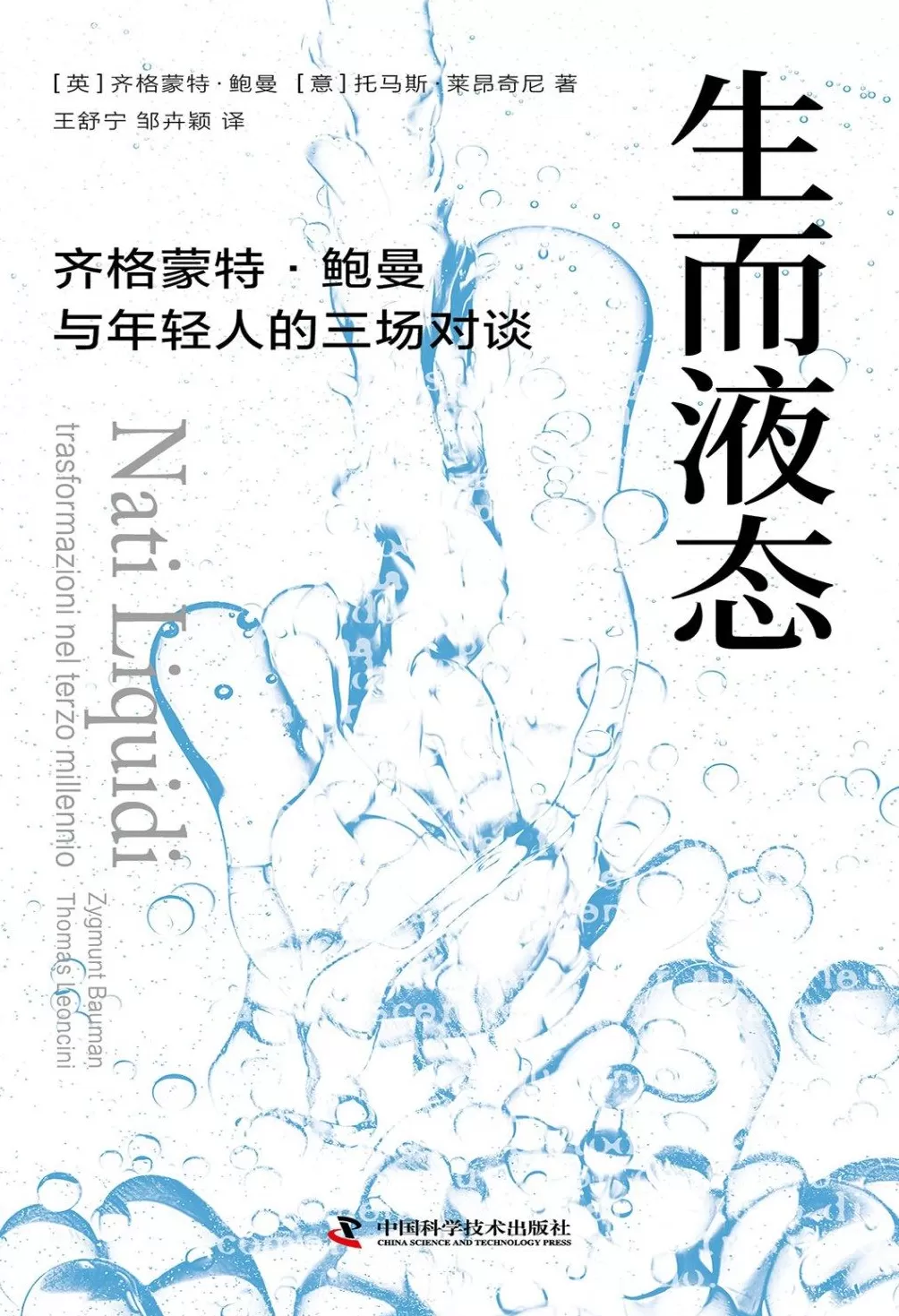
《生而液态》
与托马斯·莱昂奇尼合著,王舒宁、邹卉颖译,2025年6月出版,为国内首次翻译引进
原作名:Nati Liquidi,2017年出版
“网络并没有服务于扩展和促进人类的融合、相互理解、合作和团结,相反,它加剧了孤立、分离、排斥、敌意和冲突的行为。”
“恶已经真正而完全地被平庸化了,其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我们已经或即将对恶的存在和表现变得麻木。作恶不再需要动机。”
本书是鲍曼晚年与意大利记者托马斯·莱昂奇尼展开的三场对话,两位对话人之间恰好相差六十岁。这场跨越代际的对谈不仅承载了这位历经近一个世纪岁月的学者向后辈传递思想的努力,也始终萦绕着他对现实世界与个体命运的关切。正如书名所示,本书探讨了“液态”作为当下的根本生存处境如何深刻影响年轻一代的生活。当代社会失去了传统社会“固体”般的稳定形态,人际关系、职业、身份乃至价值观念都变得短暂易变。在鲍曼看来,这种流动性既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也构成了当代人自由与焦虑的共同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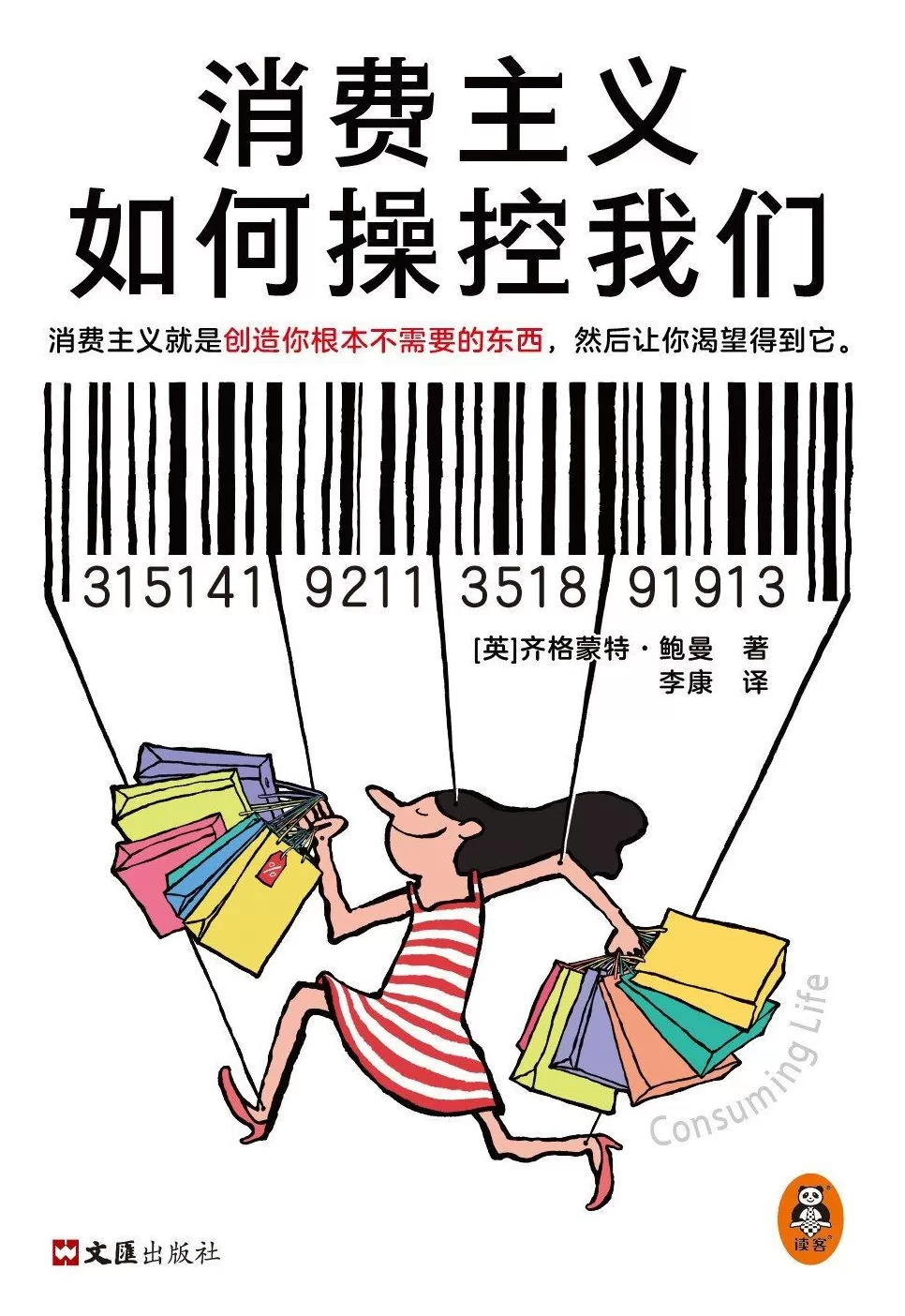
《消费主义如何操控我们》
李康译,文汇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为国内首次翻译引进
原作名:Consuming Life,2001年出版
“在消费社会,每一次消费之后产生的不是满足,而是更多的消费欲望。”
“消费主义将快乐定为评判一切的唯一标准,将不快乐视为一种应受惩罚的罪行。它向人们承诺:消费能给人快乐,并且是即时的、永续的快乐。”
鲍曼犀利地揭露了消费主义作为“过剩、浪费且充满欺骗的经济学”的运作逻辑及对生活意义的侵蚀。消费主义通过刻意诋毁未消费商品、制造“天生过时”的产品特性,让欲望永远处于未满足状态,迫使人们陷入“消费——贬值——再消费”的循环。它还重塑时间观念,鼓吹“当下主义”,将迟疑定义为损失,催生出匆忙的消费行为。不仅如此,消费主义将个体价值与消费能力绑定,把人际关系异化为商品交换,使“消费者融入商品的海洋”。幸福被简化为即时享乐,不消费被贴上“失败”标签,最终导致个体在物质堆砌中陷入空虚与孤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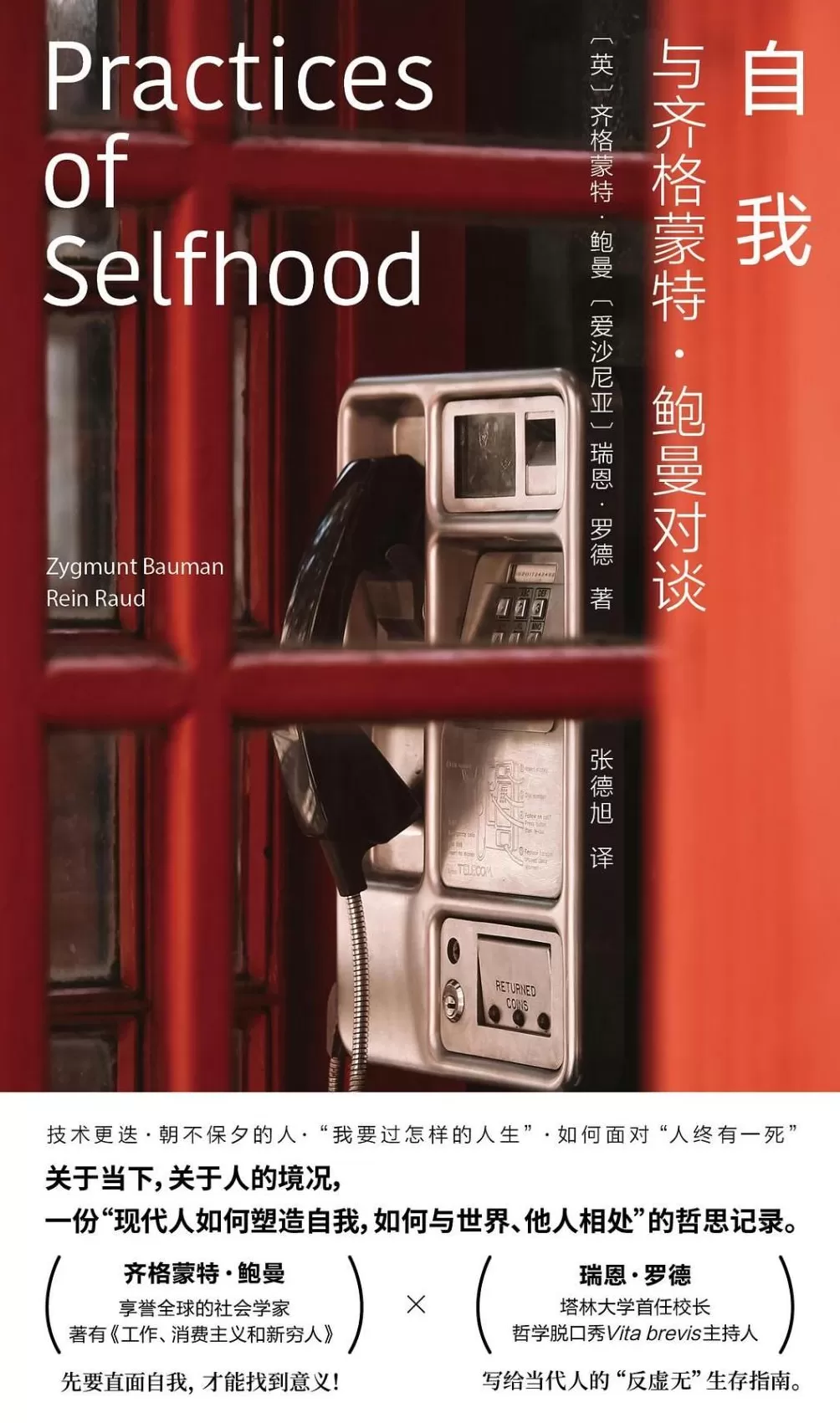
《自我: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
与瑞恩·罗德合著,张德旭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为国内首次翻译引进
原作名:Practices of Selfhood,2015年出版
“你选择的人是你自己的镜像,你也是他们的镜像。”
“自我与世界接触的每一刻,都必须选择如何理解世界,自我便由此诞生了。”
本书由鲍曼与塔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瑞恩·罗德的邮件往来整理而成,探讨自我在不确定社会中的构建困境。新自由主义语境下,现代自我是一个持续重构的动态过程,“自我实现”被异化为“持续保持灵活性的焦虑追逐”——人们为适配快速变动的社会,不断切换身份标签,却陷入“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意义真空。位于思想光谱上不同位置的鲍曼和罗德二人,用敞开的心态探讨现代社会带来的语言碎片化、表演自我、技术主义等种种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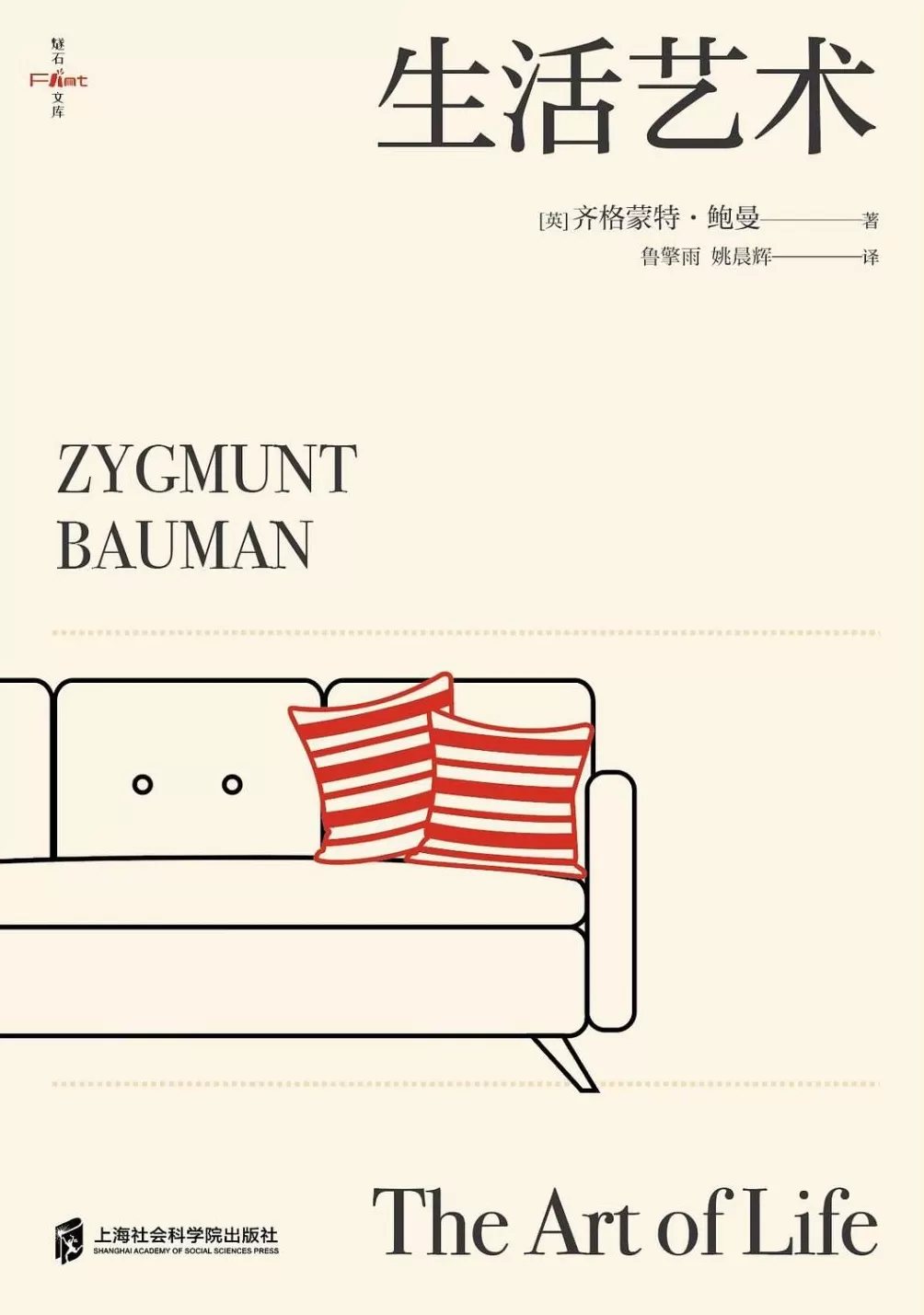
《生活艺术》
鲁擎雨、姚晨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为国内首次翻译引进
原作名:The Art of Life,2008年出版
“我们的生活是艺术品。不管我们知道,还是不知道,也不管我们是享受,还是哀叹,它都是一个事实。”
“作为个体,我们正在实践的生活方式被预先解释为我们的个人选择。一旦被塑造为个体,我们就被鼓励寻求社会对我们生活方式的认可。‘社会认可’意味着,个人实践的生活方式是有价值的、体面的,并因此得到其他有价值且体面的人的尊重。”
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我们都是“受命”成为“生活的艺术家”,都期望通过运用自身的技能和资源赋予生活以意义和形式。社会反复灌输我们“生活艺术的目标应是幸福”,但幸福的标准却在持续流动,而且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未实现的状态。本书并非一本设计指南,正如鲍曼所指出的,生活艺术的核心在于“自主建构”,充满流动性和消费主义的现代社会一直在影响我们如何生活以及看待自己的人生,但无法完全决定我们的选择,个体应在责任伦理下展开对幸福的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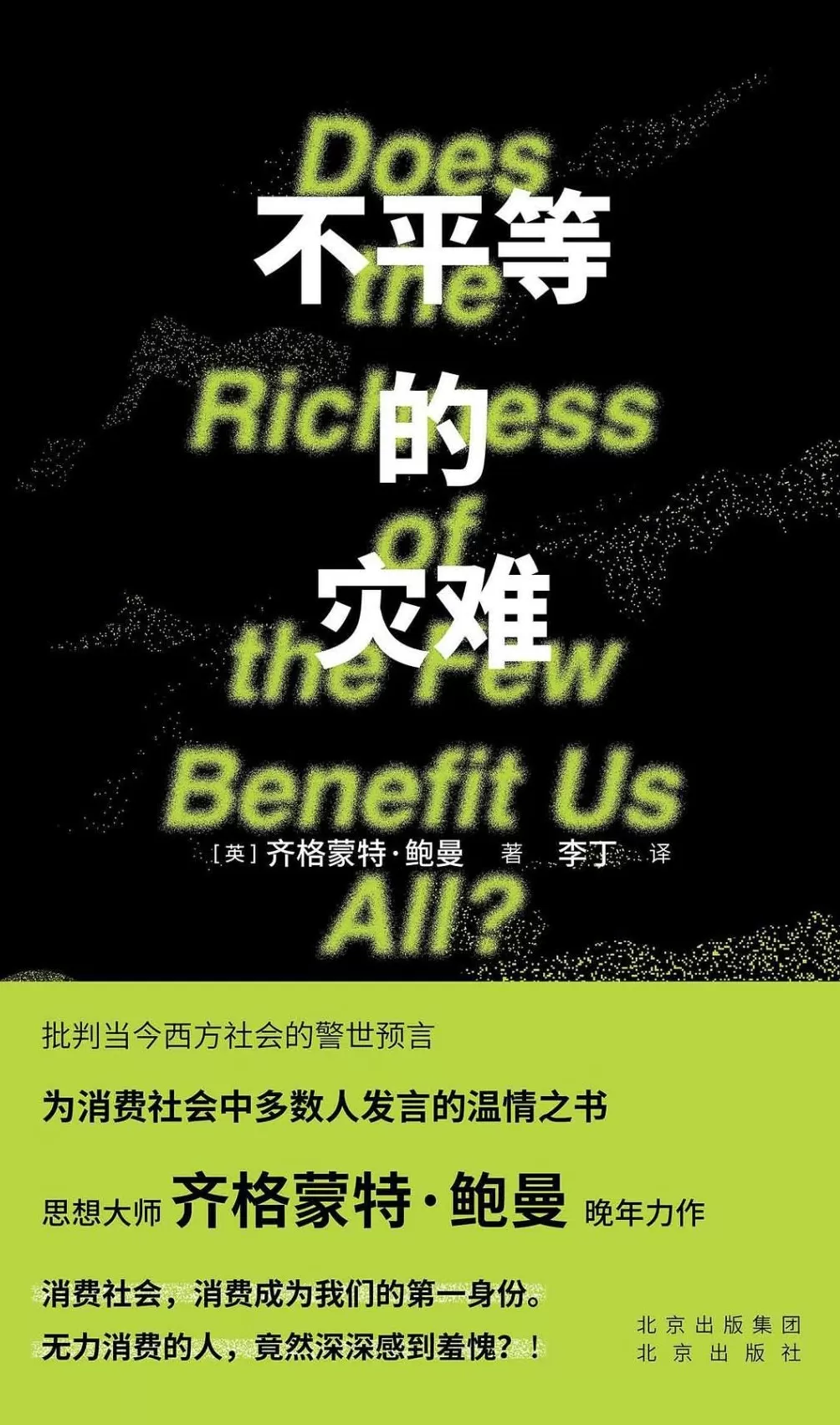
《不平等的灾难》
李丁译,北京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为国内首次翻译引进
原作名:Does the Richness of the Few Benefit Us All?,2013年出版
“我们在人生所有或绝大多数游戏中反复投掷的那颗骰子,多数时候是向着那些从不平等中获利或试图从中获利的人。”
“高人一等本身就假定了不平等。社会不平等是‘高人一等’天然的栖息之所和生养之地,同时也是它的结晶和产物。高人一等的游戏意味着,修复迄今为止不平等所造成的伤害的方式是进一步的不平等。”
本书延续了鲍曼对资本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分化的关注,旨在驳斥新自由主义“涓滴理论”认为的“少数巨富造福众人”的观点,认为这反而会加剧社会不平等。鲍曼戳破了使人们接受“富人理所应当获得更多利益”的四大谎言:经济增长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途径、持续消费是获得幸福的唯一方式、社会不平等是天然和自然的法则、竞争是社会公正和再生产的充要条件。他相信,团结与合作才是始终值得追求的价值——尽管可能在现实中面临高昂代价和巨大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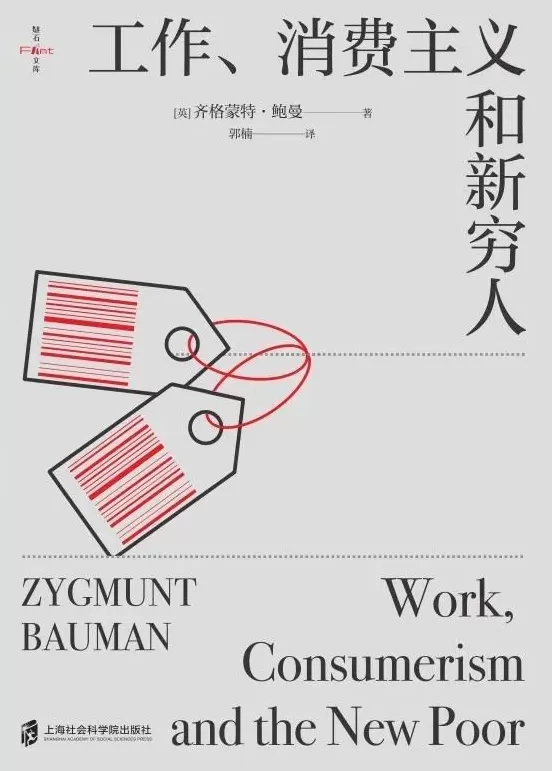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郭楠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2023年10月小开本出版
原作名: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1998年出版
“工作伦理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摒弃。”
“当今社会主要把其成员看作消费者,其次才部分地将其成员看作生产者。想符合社会规范,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就需要对消费市场的诱惑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需要为‘清空供给’作出贡献,需要在经济环境出现问题时,积极参与‘消费者主导的复苏’。”
在这部著作中,鲍曼深刻剖析了“工作伦理”的演变以及“穷人”身份的历史变迁。在现代社会早期,工作伦理被创造出来,旨在说服人们服从工厂纪律,培养努力工作是一种道德责任的观念。而进入消费者社会后,社会的逻辑发生了根本转变:人们的身份认同不再主要由其职业决定,而是由作为消费者的选择和能力来定义,相应地,“贫穷”的含义也从物质匮乏和失业,转变为“有缺陷的消费者”(即“新穷人”)的困境。鲍曼的分析揭示了社会如何通过将贫困归因于个人失败,从而系统性地将穷人排除在正常社会生活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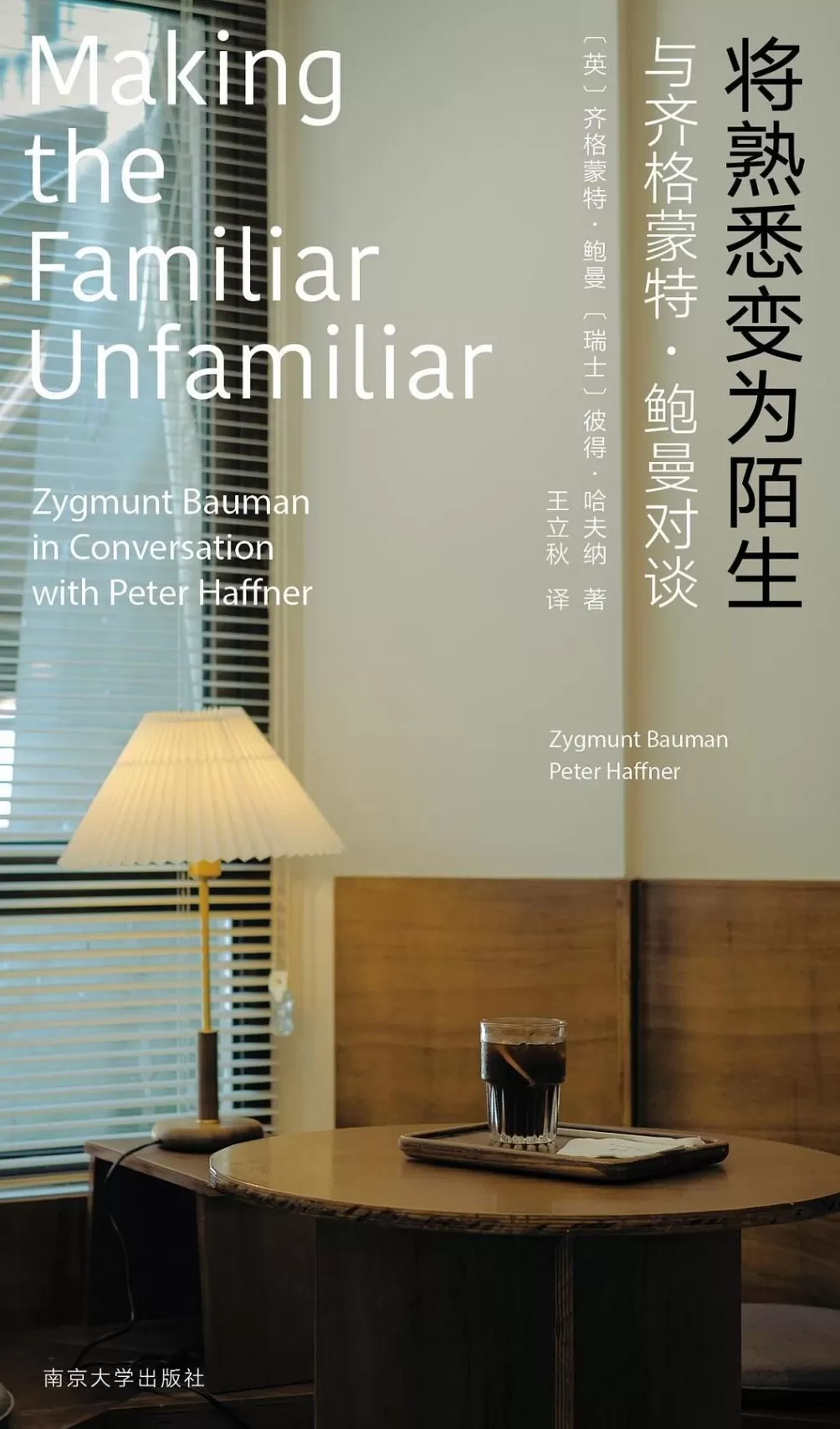
《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
与彼得·哈夫纳合著,王立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为国内首次翻译引进
原作名:Making the Familiar Unfamiliar,2020年出版
“思想始于异端,继而化作正统,最终止于迷信。这是历史上一切思想的命运。”
“知识分子的存在,是为了观察社会上正在发生什么,这个任务远远超越了一个人有限的个人或专业兴趣。知识分子要为自己国家的人民服务。”
本书来自鲍曼晚年在他英国利兹的家中与瑞士记者彼得·哈夫纳进行的四次深度对谈。作为鲍曼生前最后的访谈录,本书堪称其毕生思想的浓缩集锦。两人的交谈在“流动的现代性”这一理念框架下展开,涵盖了爱情、工作、民族、宗教、道德等现代社会的核心议题,为这些熟悉的日常概念提供重新审视的可能性。鲐背之年的鲍曼不再相信“良好社会”的存在,但仍然还是选择做一个“心怀希望的人”,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坚守个体的道德“重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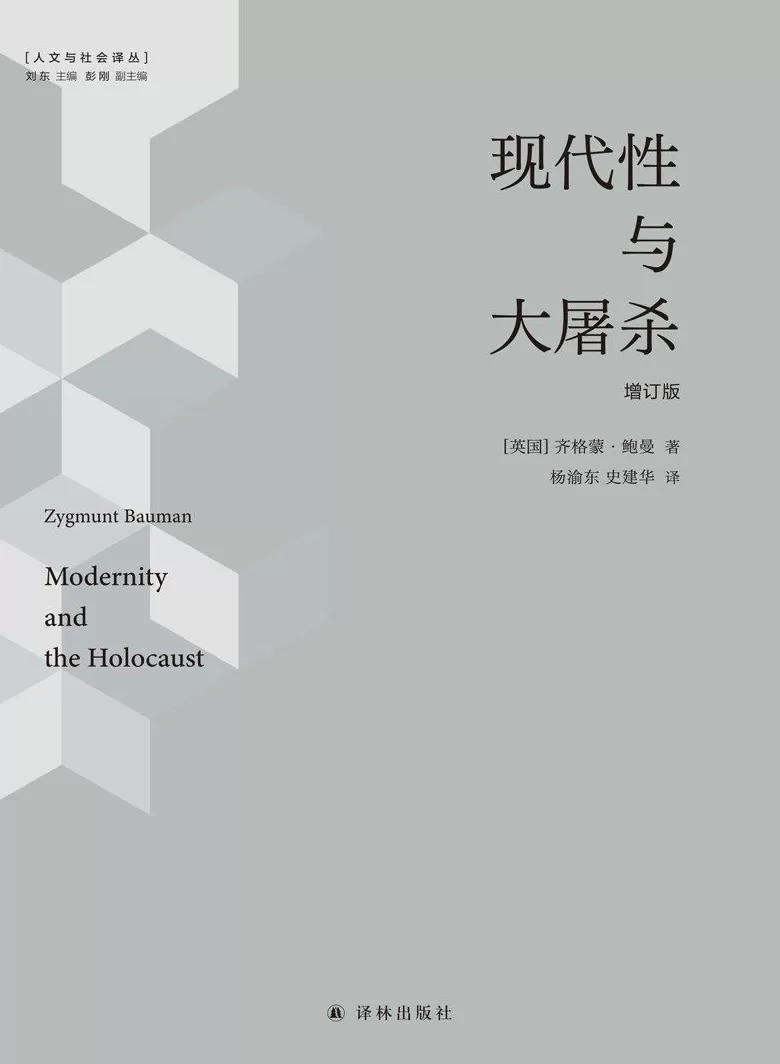
《现代性与大屠杀》
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首次翻译出版时间:2002年
原作名: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1989年出版
“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
“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于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无可指责且未受挑战的秩序的统治。”
作为鲍曼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之一,本书尖锐地指出大屠杀并非独一无二的反犹主义事件,亦非普遍人性的极端爆发,而是现代性固有的潜在可能。现代文明的核心要素为大屠杀提供了滋生土壤——科学理性的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社会管理的工程化与官僚体制,为大规模灭绝提供了高效工具和“去人性化”的行动环境,共同促成了这场集体暴行。鲍曼由此指出现代性的内在悖论:高度的文明与极端的野蛮实为一体两面,而避免悲剧重演的关键,在于每个个体在系统面前坚守无条件的道德责任。







还木有评论哦,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