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式园林的秩序》是北京大学教授朱良志的中国园林美学研究之作,以“美丽的无秩序”为核心,结合历代诗歌、散文、笔记等文献资料,详解造景、借景、气脉、曲径通幽等概念,阐释了古代造园家的艺术理念,以及中国人的生命哲学。本文摘自该书,澎湃新闻经浦睿文化授权发布。
真正的园,是让你放弃拥有,淡化园林的观念,融于天地中。古人说,画到无画,是谓能画。也可以说,园至无园,是谓真园。古人在这方面颇有慧解,兹举其三:
一是“借天为园”。传统园林说借景,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天借”——小园是借景于天之创造。“中为天地物,今为鄙夫有”,偶尔为我所有,以一座小园汇入宇宙中,如一片落叶归于空山。茫茫天际,尽为我园。白居易说:“天供闲日月,人借好园林”,人之所造,乃是借天地之景,偶然为之。天不能言,人代言之。开辟园林,代山灵立言,为其开生面。正因此,一座小园,切莫认为是自己的,“我园”的执念是要破除的。
元杨维祯( 1296—1370)《借巢记》,通过一段对话,谈借天为园的道理:
客有号鹤巢者,自杭而苏而松,率假馆以居。予一日过其馆,改命曰“借巢”。或有笑者曰:“鹄有巢,而鸠借之,鸠之拙也;鹤不能营一巢而借,亦拙甚矣乎!”杨子哑尔笑曰:“子亦知夫‘借’乎?人一身外为长物,物皆借也。吾试与子言借:衣冠借以束身,棺椁借以掩胔,土石借以周郭,山岳借以积土,天地借以奠岳。极之于大,则大灵借以辟天地,何莫非借也?……吁,借乎借乎,何啻于一巢乎!”或者起谢曰:“浅矣乎,吾之窥借也,吾因子言‘借’,而知天地万有之不有于我也。”杨子曰:“吾于天地万有皆借也,而有不借者在。”“何在也?”曰:“以天地万有之借为借者,万有之客也;以天地万有不借之借为不借者,不客于万有之客者也。子徒知吾有借,而庸讵知吾不借之借,而不客于客者耶!”“不客者谁?”曰:“问诸有物,有物问诸有初,有初问诸有无,有无不可名全,以名其巢居。”
人的生命是偶然的,是“借”来的,如一片落叶飘于空山,无一物属于自己,“吾于天地万有皆借也”,何况人所作之园,那只不过是寄客的借居。小园借天借地而成,归于天地,也就找到了归宿。人唯有超越物我相对的态度,也就是他所说的“不借之借”——不以此身之借为借,“不客之客”——不以身之为客为客,超越主客之分别,超越我物他物的拣择,才能有充满圆融的生命。
容园,是清时扬州著名的私家小园,初建于乾隆时期,嘉、道时仍存世,在阙口街流芳巷内,梁章钜曾客居此园。初建园主为汪漋(1669—1742),安徽休宁人,占籍扬州,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官至巡抚。其《容园记》云:“其第在城之东南隅,旁有地数百弓,于是垒石为山,捎沟为池,导以回廊,纡以曲榭,杂植嘉葩名卉,几榻琴尊,相与分张,掩映而并,自署曰‘容’。‘容’之云者,非容膝之谓,盖直以良辰美景,优犹以容其养;一丘一壑,徜徉以容其身。”他取的是在天地屋檐下容身之意,让天地容下自己。天地不容于人,皆因人常将自己从天地中隔出来,以霸凌的态度对待托养之所,最终为天地所弃。容园之园,借天为园,人天合一,此为文人园家之怀抱。
二是“不知有园”。从创造的角度说,以超越园的观念来建园,方有真园。如俞樾在《曲园记》中所说:“曲园者,一曲而已,强被园名,聊以自娱。”如同老子“强字之曰道”,称之为园,也是勉强言之。他的意思是,为园者不能念念在园,精雕细刻,做不出好园;常以自己所居为园者,最终园会成为其牢笼。文人园重视脱略于形式之外的创造,园林之妙,在其格局,在其情趣。“一旦忘却‘园’,而沉湎入‘画’,他就不再感受到尘世浮沉的烦扰。”(童寯《论园》)拳石与勺水,聊复供流连,文人小园让你忘却对象化存在的世界,融于自己的生命节奏中。
文人园的概念与那些靠园林显示身份、炫耀财富和权威的观念不同,它受“无名”的思想驱动,以平等的觉慧来营造,靠谦卑来亲和花鸟虫鱼,以天心来雅聚天下同侪。淡化园林的存在,也成为文人园的核心观念——造园者不以园为园。
钟惺(1574—1625)的“天下皆园”的观念,表达的就是这淡化园林的思想。《梅花墅记》说:
出江行三吴,不复知有江。入舟舍舟,其象大氐(抵)皆园也。乌乎园?园于水。水之上下左右,高者为台,深者为室,虚者为亭,曲者为廊,横者为渡,竖者为石,动植者为花鸟,往来者为游人,无非园者,然则人何必各有其园也?身处园中,不知其为园,园之中各有园,而后知其为园,此人情也。予游三吴,无日不行园中,园中之园,未暇遍问也。于梁溪则邹氏之惠山,于姑苏则徐氏之拙政、范氏之天平、赵氏之寒山,所谓人各有其园者也陇朝雊,斯之不远。
“园之中各有园,而后知其为园”,因为有园的界限,就有是园非园的分别;有了这样的分别,就失落了水乡泽国皆为园的妙意;失落了这样的妙意,人就落在风景中。“人各有其园者也,然不尽园于水”,未尽于水意,未尽于山意,未尽于天地之意,框在园中,所以执着于园者,便失落了园的真意。钟惺认为,天下皆园,“身处园中,不知其为园”——心中不存园,自是有园者。
作为文人园的范式,辋川模式其实就在淡化园林的界限,是一种无园之园的模式。借无边山林、幽邃宇宙,为我性灵文章。山林为园,也就没有了园林界限,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说:
近腊月下,景气和畅,故山殊可过,足下方温经,猥不敢相烦,辄便独往山中,憇感配寺,与山僧饭讫而去。比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舂,复与疏钟相间。此时独坐,僮仆静默,多思曩昔,携手赋诗,步仄径,临清流也。当待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鯈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雊,斯之不远。
从他的辋川诗二十首,乃至传世《辋川图》摹本等都可看出,他造园,意在体会天下皆园的“深趣”。山林广阔,天地一体,所谓“城上青山如屋里,东家流水入西邻”,他在无园中体会浑然一体的生命之意。今人曾有关于辋川二十景是否为真正意义上的园林的讨论,就与王维有意模糊园与非园界限的观念有关。
张岱的快园,是他年幼时读书的地方。明清易代,快园便归荒烟中。国乱稍定,他重临旧地,修复废园,感怀系之,作《快园十章》,简短的序言说:“己丑(1649)九月,僦居快园,葺茅编茨,居然园也。诗以志之。”张岱的“居然园也”,涉及园林的概念,什么样的形式可称为园林?陶渊明的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是否可称为园林?园林的存在界限其实是模糊的。文人园如同绘画,可以是长卷,如弇山园、愚公谷、寒山别业,也可以是随意而作的小品,如高士奇的江村草堂。甚至可以是一帧扇面,如赵昱春草园的断面。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居然园也”,文人园必须体现出园家的生命情趣,不为外在秩序左右,它是身体歇息的地方,更是灵魂休憩的地方。快园虽然比不上祁彪佳缜密构思的寓山园,但照样有其诱人风致。这样的传统,可谓文人园的当家风色。
高士奇的江村别墅,就是一个似园又非园的所在。高士奇在《北墅诗·蔬香园》序云:“余官京师,取菜根有味意,以蔬香名园,今归北墅,手自携锄,督课种萟墅中,有屋一区,在香芹涧外,尽取隙地,栽植瓜菜,甘旨之余,足娱宾客。昔人所谓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并有诗云:“藻羞王公,葱薤进君子。虽笑樊迟陋,犹胜何眉侈。我无肉食相,乐志在蔬水。年来窃微禄,素餐真可耻。一卷种植书,探索得妙理。小圃幸未荒,灌畦自今始。早夜忘作劳,吾师杨伯起。”这简直有陶渊明归园田居的风味。文人小园多是淡化园林意味的小园,似园非园,这在王时敏的乐郊园、赵昱的春草园等中也能看出。刻意为园,为文人园家所排斥,山林谷地,果蔬林薮,种花莳草,也有园观,也是园事。陶渊明的园林观,铸造了文人小园的体式。
三是不系于园。园者,名也,园乃“名”之宾。从形式上说,它与普通人的居所不同,依照美的规律创造,是一片好风景,此为“名园”;从拥有者说,它为“我”拥有,由此便有了界限,此为“我园”。文人园要超越“名园”“我园”的执念。南朝徐勉(466—535)《为书诫子崧》中写道:“常恨时人谓是我宅。古往今来,豪富继踵,高门甲第,连闼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谁室?但不能不为培塿之山,聚石移果,杂以花卉,以娱休沐,用托性灵。随便架立,不在广大,惟功德处,小以为好。”园之所属,属天。建园,不以园为园,唯是托付性灵而已。一说园林,即落风景,不知有我,方近妙道。
清陆以湉(1802—1865)《冷庐杂识》卷六有《不系园》一则,其云:
明季钱塘汪然明孝廉汝谦,啸傲湖山,制一舟名“不系园”,题诗云:“种种尘缘都谢却,老耽一舸水云间。”又作《不系园记》,其略云:“自有西湖,即有画舫。武林旧事,艳传至今,其规至种种,不可考识矣。往见包观察始创楼船,余家季元继作洗妆台,玲珑宏敞,差足相敌。然别渚幽汀,多为双桥压水锁之,不得入。癸亥夏,偶得木兰一本,斫而为舟,长六丈二尺,广五之一。入门数武,堪贮百壶,次进方丈,足布两席。曲藏斗室,可供卧吟,侧掩壁厨,俾收醉墨。出转为廊,廊升为台,台上张幔,花晨月夕,如乘彩霞而登碧落。若遇惊飙蹴浪,欹树平桥,则卸栏卷幔,犹然一蜻蜓艇耳。中置家僮二三擅红牙者,俾佐黄头以司茶酒。客来斯舟,可以御风,可以永夕,远追先辈之风流,近寓太平之清赏。陈眉公先生题曰‘不系园’,佳名胜事,传异日西湖一段佳话,岂必垒石凿沼圉邱壑而私之,曰‘我园我园’也哉?”
汪然明(1577—1655),字汝谦,官孝廉,为徽州歙人而居杭州,啸傲湖山,优游西湖,经商致富,又膺文情,尝作一小舟,名“不系园”。此不系之舟在当时很有盛名,也成为文人雅集之所,董其昌、张岱、陈继儒、黄汝亨、陈洪绶等都曾来不系园中,这里载动着文人的性情风流。不系园是一画舫,取《庄子·列御寇》“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之意,名为陈继儒所题。客来斯舟,可以御风,可以永夕,说生命的从容,说为园者超越园的快慰。《不系园记》中所说的“岂必垒石凿沼圉邱壑而私之,曰‘我园我园’也哉”,是文人园家的透脱见解,君看一叶舟,出没风烟里,那就是他们的生命之园。
石涛曾作《蜻蜓叶》图,图中苍岩古木,江气迷漫,一客棹舟,中流容与。自题绝句云:“且学蜻蜓傍水涯,从今款款不须家。老夫眼窄何由放,出没无踪点浪花。”所画即为“不系园”情怀。别无归处是吾归,没有目的地,那无际的天涯,就是生命的归宿。秉持“中为天地物,今为鄙夫有”的文人小园,是天涯之间的创造,需要超越为园的执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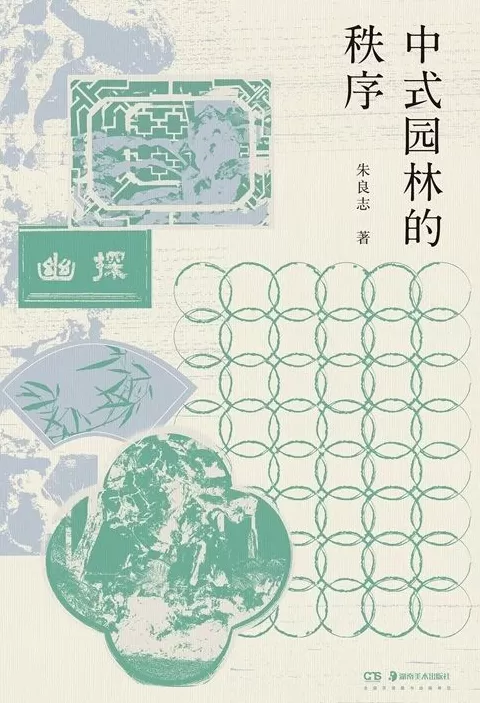
《中式园林的秩序》,朱良志著,浦睿文化|湖南美术出版社2025年10月。







还木有评论哦,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