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头一回生娃,就体验了一把“硬核”模式:没有队友支援,没有物资补给,单枪匹马去住院,最后要手术了,麻药居然还未见效——
够刚猛,够彪悍。
当然,无奈的成分居多,人大多数的彪悍,不过是环境逼出来的勇敢,何况是一个高龄孕妇。老大出生前几天,队友因为想把家里安排得更妥帖一些,匆匆忙忙下班的路上遭遇了车祸,断了三根肋骨。至今还记得,我挺着巨大的肚子,来回穿梭于床的两侧,把席梦思一点点挪到地板上——只为把床变矮,方便他坐。我也能单膝跪在床上,一手撑住床板,一手托住他后颈,缓缓将他放下,慢慢托他起来。
婆婆、妈妈的关心在天上,预约的月嫂暂时无法到岗,里里外外全靠我一人张罗。身强体壮的我,倒没觉得有多么伤感。记得在华师大读书时,校医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撼动我智齿半分,她气势汹汹又气急败坏扔下一句:“你的牙齿和你人一样强壮!”直到我嘴角被撬烂红肿,火辣辣地疼,她才拔出了半颗牙齿。
是的,半颗。跟苹果里吃出的半条虫子一样让人惊恐,然而需切开牙龈才能取出另外半颗牙的惊恐更胜一筹,我只好选择与那半颗残牙共存,没想到,冒险成功了,相处很和平,平日里动不动就兴风作浪的智齿,从此风平浪静了。
也许,退一步,果真是海阔天空。
于是,我也安然接受了和“残存”的另一半和平共处。我安慰自己:照顾照顾他,多活动活动,没准更有利于顺产。可是,肚子里的娃心疼我,他发出了无声的抗议,几乎不怎么动了。我赶紧去医院吸氧,但他执拗得很,几次检查数据都不好,我便被强制入院监护。
简单的住院用品是我回家收拾的,入院手续也是我拎着大包小盆独自办理的。护士看着形单影只的我,很是诧异:“你,一个人?”我笑了:“是啊,一个人,给拥挤的医院腾点空间,再说,你看我这年纪,也不像是需要躲躲藏藏的小三,是吧。”一句话,把我们都逗乐了。
我可以坚强,但我的坚强,却未必是肚子里孩子的铠甲。他本就因我的奔波劳累而战战兢兢,住院后更是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我曾趁护士不备,“越狱”回家过,但第二天被严肃警告,让我后果自负,我便再没那个胆量了——终究是担心孩子突然发动,而我的“后援团”还未成团。
六人间的病房实在太热闹,啼哭、呻吟、安抚、耍小性儿,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我无处可逃,只好坐在走道的折叠椅上看书,看的还是大部头专业书,也许是博士后出站的压力在作祟,烦恼被放大了。然而这深夜苦读的一幕,在查房的护士长眼里,成了令人心疼的诗意。她于心不忍,当即为我协调了一间紧俏的单人间。
史铁生在《我二十一岁那年》里写过,他因为爱读书而被大夫护士关照,住进了当时他能住的最好的房间,她们以此成全一个病情不容乐观的年轻人安静读书的愿望。如今,护士长也用这份跨越时空的善意,庇护了一个无人陪伴的高龄产妇渴求睡眠的无助。
睡眠稍得安顿,意外却不期而至。在住院的第5天,胎儿再次受到惊吓。为助顺产,我和几位孕友晚饭后在楼梯间来回散步。“一孕傻三年”真不是虚言,不然,对于一个莫名其妙加入到我们队伍的中年男子,我们怎么会一点儿警觉都没有?他自称家属,抱怨老婆不听他劝,在这里剖了腹,又说他有门路能保证我们顺产,还问要不要转院。我们这才觉出不对,转身欲回病房。因为人多势众,起初并不害怕,谁知走到楼梯间与走廊的连接门时,这个人突然掀起我的病号服,随即夺门而逃,留下我们一行人惊恐地僵在原地。
事后查监控,才发现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家属。那一夜,后怕如潮水般涌来:万一遇到了心理变态或不法分子,万一孩子受了伤,万一他还躲在周围的某个角落——我心神不宁,彻夜难眠。再“硬核”的妈妈,孩子永远都是她的软肋。
这动荡的宫内环境,孩子怕是忍无可忍,他迫不及待要出来了。第二天一早,我破水见红,正当我满心欢喜,鼓足勇气,准备打一场硬仗,热烈欢迎孩子的到来时,医生宣布:羊水浑浊,必须立即剖宫产。可想而知,等我家那位断了三根肋骨的家属一步一挪来医院签字,不知要耽搁到何时。手术一等再等,终于还是在12:10开始了,饥肠辘辘的医生,宫内窘迫的孩子联手把我推向了一场麻药还未见效就开始手术的“硬核”狂欢。
手术刀切下的瞬间,我才真正体会到何为“硬核”,那活生生被撕开的灼痛让人痛不欲生,失声大叫。医生说生孩子哪有不痛的,忍一忍。可如何能忍?只觉得五脏六腑被一股巨力狠狠撕扯,拽出,弹回,再拽出——如今讲述起来云淡风轻,但当时,我唯有咬紧牙关,一秒一秒数着时间。
突然,一声怯怯的啼哭,不算嘹亮,却像一道光驱散了笼罩着我的无边创痛,我开始变得轻盈,舒展,松开了所有紧绷的弦。原来,万里跋涉,真的只为了这一刻的安恬。撕扯的痛感消失了,只剩缝合时的拉扯和紧绷。不过,没有关系,我的全部心神都在孩子身上了,他一直在哭,被医生冲洗,瑟瑟发抖,我巴巴地望着,盼她们动作快些,再快些,盼孩子能早一刻被包裹,早一刻感受到温暖。可怜的孩子,这人世间的动荡可是比子宫里要厉害一万倍啊。
如果不是后来生了老二,有了对比,我至今都不知道原来剖腹产手术过程中是没有痛感的,那隐隐的痛是在麻药退去,回到病房后才开始的。当然,也是因为有了生老二后的虚弱,我才知道当年的我在刚刚被医生允许下床,便能抱着孩子去串门该是多么生猛。
痛就痛吧。至少,我的孩子没有挨过麻药的痛击,免受了药物的侵扰,算是“绿色无添加”了,这么一想,顿时释然,所有的委屈也一笔勾销了。

作者和她的两个娃。
出院那天,一直对我照顾有加的护士长笑着说,“大红,你还没生到女儿呢,下次再来哦!”我以“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为由谢绝了她的好意,并祝愿她的专业和善心能惠及更多年轻人。如此“硬核”的生产,一生一次,足矣。
或许是我表现得太过彪悍,连上帝都觉得这属于驾轻就熟——五年后,他竟又给我发来了一纸“报到通知”。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一次,我迎来的,依然是个男孩。
如今,养育着两个混不吝男孩的我,在一次次“越过山丘,却发现无人等候”,在一次次“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之后,终于更深刻地理解了“硬核”的含义:它是倔强,是强悍;然而,它的尽头是柔韧,是和解,是用智慧和耐心,将生活的刀光剑影缓缓炼成的通透月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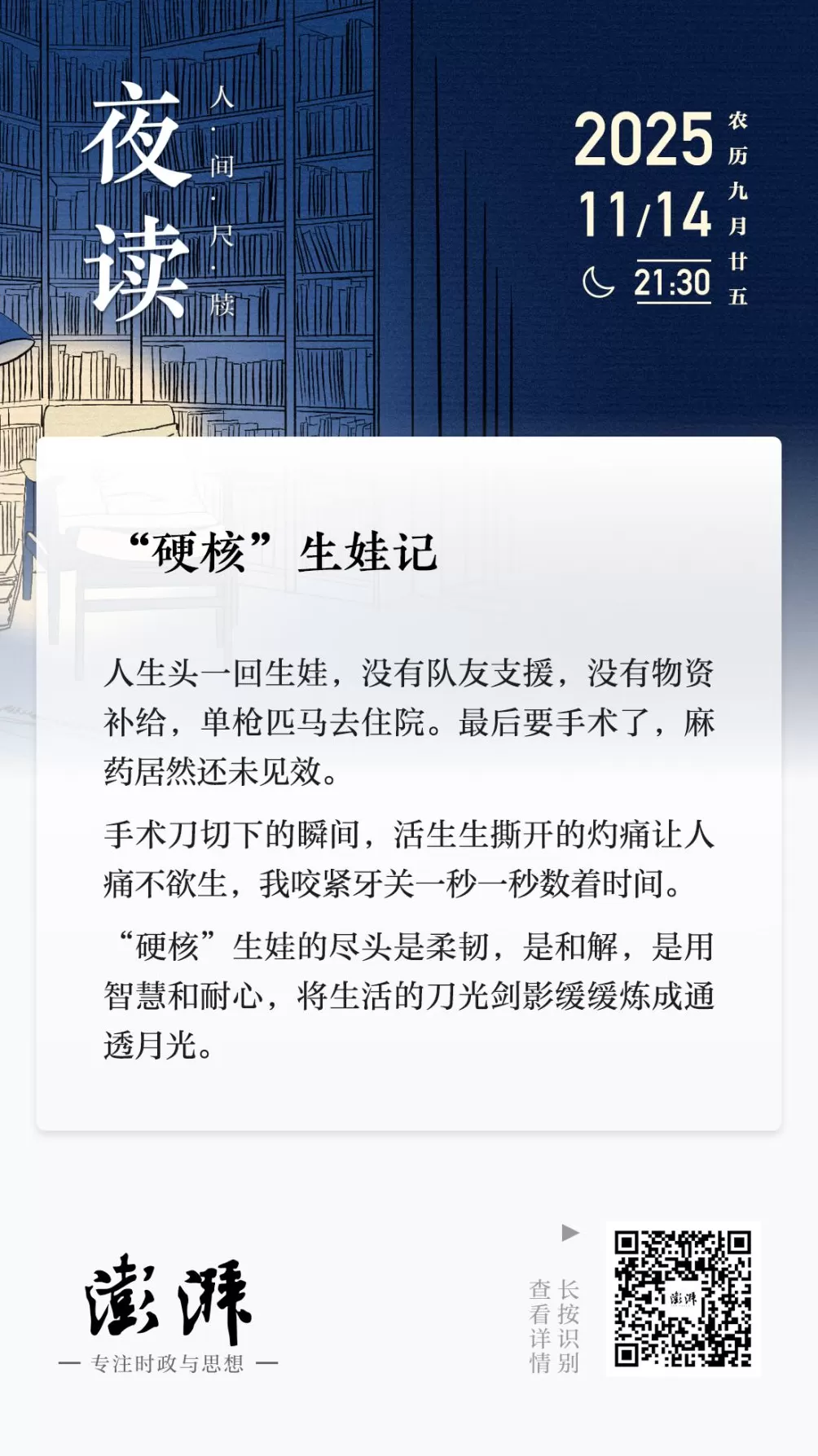







还木有评论哦,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