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咖啡馆、网红餐厅、网红景点、网红街道、网红城市……不知不觉间,“网红”已经变得无处不在,改变了附近和远方,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网红究竟指什么?在数字空间发生的网红文化如何影响线下的城市空间?这些问题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人文地理学者Carwyn Morris的研究兴趣所在。
2005年,刚刚高中毕业的Carwyn在间隔年从英国乡村来到中国甘肃,在天水的一所职业学校当英语老师。接下来的十年间,他见证了中国城市空间和数字文化的飞速发展,将个人的经历和兴趣变成了学术旨趣。在对重庆李子坝地铁站、长沙文和友餐厅和北戴河阿那亚度假地产等网红地标的研究中,Carwyn和他的学术伙伴提出了“网红都市主义”的概念,用以描述数字奇观和城市空间的循环互动。
Carwyn认为,网红首先是一个与受众(audience)有关的现象,是那些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内容、分享经验的人让网红塑造的循环得以开始并不断重复。2022年开始,Carwyn和他的学术伙伴发现,一座冷门的德国城市因为发达的亚洲饮食文化在中文社交媒体小红书上成为了“网红”,于是开始了对杜塞尔多夫的研究。2025年春天,Carwyn接受了小红书的邀请,踏上了重访杜塞尔多夫之旅,这次旅程被拍摄成了纪录片《寻找杜塞尔多夫》(a flâneur and Düsseldorf),于北京时间10月26日在中德两地同步放映。

《寻找杜塞尔多夫》(a flâneur and Düsseldorf)纪录片剧照
近日,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对Carwyn进行了专访,从他的个人经历出发,谈到他关于网红与城市的研究,以及拍摄纪录片的发现和思考。在Carwyn看来,中国是全世界城市化和数字文化最为发达也最为复杂的地方,因而最有可能诞生新的概念和理论。在一个人文地理学者的眼中,一切都与空间和规模有关,还有人的情感和认同。
澎湃新闻:请先谈谈你的个人经历,你为什么对研究中国的流动人口和数字文化感兴趣,这和你的成长经历以及在求学、工作过程中的迁徙经历有关吗?
Carwyn Morris:我长大的地方是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一个300人的小村子,现在大概有350人。2005年高中毕业后,我开始了间隔年。来中国其实是一个意外。当时我申请了一个慈善机构的志愿项目,经过两轮选拔之后,我被要求填一份表格,在上面勾选三个有意愿前往的项目地。当时的我是一个喜欢日本动画和电子游戏的青少年,所以我的首选是一个北海道的项目,第二选择是一个参加过这个项目的朋友推荐的泰国,然后我看了一下地图,发现在日本和泰国中间有一个中国的项目点,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就选上了,结果我就被派到了甘肃天水,在一所职业学校当英语老师。
天水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偏远的小县城,很多人可能是因为去年清明前后天水麻辣烫成为网红才知道这个地方的,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天水也是一个大城市。我教的学生学的是酒店管理和幼儿教育专业,他们会用QQ和已经毕业的朋友交流,很多人会打《反恐精英》。他们都准备在毕业后成为流动人口,去更大的城市发展。而我在英国小村的时候,在网络上看到全世界,我和他们的感受是有些相似的,我也想去体验充满活力和变化的城市生活。在天水的一年里,我也会去中国的其他城市,我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正在发生:这里很有活力,好像有一种潜能,每个人都有想去的地方想干的事情,到处都在盖大楼,马上又要举办北京奥运会,所有人都对未来怀有希望……所以我不想回英国,想继续在这里发展一下,于是天水的项目结束之后我搬到了西安,在阿斯顿英语、新东方、环球雅思之类的培训机构教英文。但我也会受到我妈妈的压力,她想经常看到我,经常跟我聊天,那时候我们会用Skype,我就觉得这些即时聊天的工具和后来的社交媒体可以稍稍缓解我的这种压力,如果我多发一些内容,可能我妈妈就不会那么担心我,那么想要我回英国,我想这也是很多离开家乡的人共同的感受。
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年轻男孩,喜欢打游戏,经常买一些奇奇怪怪的电子产品。我当时有一些西安外国语大学的朋友,经常一起去夜店蹦迪。大家一起吃宵夜聊天的时候,有女生会吐槽自己的男朋友,说他是个Dota男。这让我很惊讶,因为在英国,像她们这样时髦的、受到很好教育的年轻女性是不会知道Dota是什么的,这个人群不会掌握关于数字文化或者游戏文化的知识,也不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网络用语,而在2006年的中国,数字文化已经开始融入生活,成为一种线下文化,这方面大概领先英国5年左右。从这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关注中国的数字文化了。
后来我在伦敦政经读人类学硕士,读关于中国流动人口的文献,发现这些书里讲的都是最底层的流动人口,大部分不会讲到他们的数字文化。但因为我自己的经历,我知道迁徙不一定只发生在底层,我的大部分朋友都经历了迁徙,从天水、西安到成都、北京、上海或者国外的城市,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来自底层,但大多数人的家境都还可以。所以我觉得英语世界的学者写的中国流动人口,和我看到的不一样,我就决定做这方面的研究。其实在2015年我写博士研究计划的时候,我已经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做品牌战略文化咨询的工作,收入和现在差不多,也挺有意思的,但是在业界工作的话,就没法深入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议题,所以还是决定读博。
所以,我的研究兴趣不光是和我在英国的经历有关,也是我在2005年到2015年之间在中国的所有经历、认识的所有人,让我慢慢地往这个方向走。
澎湃新闻:“网红”这个概念是如何成为你的关注点的?
Carwyn Morris:在2005年左右,我就在新闻上看到过“芙蓉姐姐”等中国网络红人的新闻,但没有特别关注。但是因为我自己打Dota、英雄联盟、Dota2这些电子游戏,所以我一直关注电竞选手。在2011、2012年的时候,我开始关注他们怎么赚钱,他们在线上的社群里面非常有名,我对于网络名人或者说网红最早的关注是因为电子游戏。

长沙网红餐厅文和友
至于把网红作为研究课题,是在2019年,我当时在做一个关于中国城市的小项目,想知道为什么很多人离开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去了像长沙这样的二线城市,我当时在知乎上经常看到有人会写:长沙是个网红城市,你不会觉得这个地方很落后,我们有超级文和友……我突然想到,2017、2018年我在北京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和朋友一起去吃东西,有一个朋友就说我们要不要去工体那边的一个网红餐厅,其他的朋友表现得很嫌弃,但还是去了,不仅吃了饭,还拍了照片,还发了朋友圈。当看到知乎网友说长沙是个网红城市的时候,我想起了以前已经去过的网红餐厅,就开始做一些研究。
后来我跟另外两个也是做人文地理城市研究的学者朋友(Amy Y. Zhang, Asa Roast)聊这个事情,他们就聊到了重庆李子坝地铁站,那个时候也有很多朋友邀请我去阿那亚,我们后来就合写了“网红都市主义”(Wanghong Urbanism: Towards a New Urban-Digital Spectacle)那篇论文。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是2015年。当时我跟在北大读博的朋友赵珞琳聊天的时候,她给我看了一些数据,数据显示2015年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点,从此以后“网红”这个缩略词超过了“网络红人”,开始被广泛使用。2016年之后,网红后面开始出现各种跟城市空间有关的词,比如网红打卡、网红旅游等等。昨天的放映会上,董晨宇教授说一旦一个词从名词变成了形容词,就很了不起,我一直以来也有这种感觉。
澎湃新闻:“网红”一词的含义包含很多层次并且在不断变化,你如何定义网红?这是当下数字时代中国的独特现象吗?Wanghong和英文世界的internet celebrity、influencer等概念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Carwyn Morris:网红肯定是一个中国概念,从字面上可以翻译成Internet fame,而英文世界用的词汇是influencer、internet celebrity、micro celebrity、Instagram hot spots、TikTok hot spots……很混乱,需要用非常多的词汇来描述这种现代的fame。全世界都有在网络上出名的人或事物,而且在全球、国家、地区、城市、街道等各个层面都会有,以前英文里面有一个说法叫“big name on campus”,指的是一个大学校园里最有名的那个人,而网红这个词特别灵活,可以把所有相关的现象都概括进去。至于是因为这个词汇本身的灵活性所以它被用来包罗万象,还是因为人们开始用网红形容餐厅、城市等等所以这个词汇才变得灵活,这很难界定,这两件事似乎是同时发生的。而因为网红这个中文词汇的灵活性,它也加速打开了网红概念的内涵,让它的形式变得更加多样化了,同样的事情没有在英文世界发生。而事实上,网络上的fame已经是现在的主流,传统的媒体、名人或许影响力比一般的网红要大,但在这个时代已经成为了少数,这是fame这个概念本身的进化。我觉得wanghong是最适合描述当下文化现象的词汇,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它。2022年我们办了一个关于“网红都市主义”的工作坊,邀请了很多研究网络上的著名地点的专家学者,刚开始他们会问网红是什么,过了两天,大家都在说这在圣保罗是个网红地标,那个也是网红,说明这个词确实很好用。中国的数字文化是最发达的,从中文当中提炼概念也是合理的。
对网红的定义是我和纽约城市大学的陈雨尘老师正在合作的一个项目,我们在检视这个词汇被使用的历史时发现,它越来越向一个空间概念移动,所以我们想要提出一种超越“人”的对网红的定义。这是一个还在进行中的研究,所以我还不确定最后会怎么下定义,但我认为网红首先是一个与受众(audience)有关的现象,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选择过程,虽然这个过程中也会有很多力量介入,但如果不是受众自发地对这个人、事物或空间感兴趣,一家公司或者其他方面投入再多的资源,也不可能制造出网红。在我们目前的模型当中,网红还与空间(Spatially relational)、欲望(Desire)、特异性(Alterity)、愉悦感(Pleasantness)、可及性(Accessibility)和暂时性(Temporality)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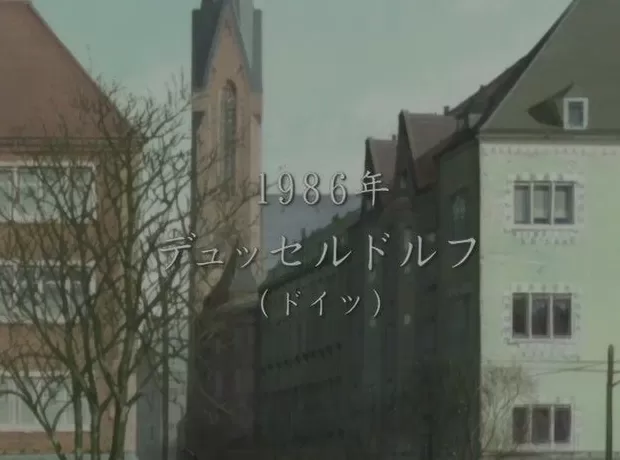
根据日本漫画家浦泽直树的同名原著改编的动画《Monster》中的杜塞尔多夫街景
澎湃新闻:你最初为什么会把杜塞尔多夫作为研究对象,后来又为什么决定参与纪录片《寻找杜塞尔多夫》(a flâneur and Düsseldorf)的拍摄?
Carwyn Morris:无论是李子坝、文和友还是阿那亚,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并且满足了受众或者说社会的某种需要、某种渴望,我觉得网红的概念模型里可能还要加上社群(community)。21世纪的前20年,世界范围内社群都在衰落,尤其是在大城市里,而参与一个网红现象,事实上也是在参与一个社群事件。比如文和友餐厅,首先它是一个很好玩的空间,也很适合拍照,但同时它提供了一种即将消失的饮食文化体验,它把传统的夜市整合进了干净整洁的城市空间里面,满足了一个群体对于某种文化的怀旧和渴望。想要真正理解一个网红城市是如何造就的,需要做很多的受众研究,但中国的网红城市太复杂了,往往代表了很多不同的叙事或情感,所以我会在欧洲城市做这样的研究。比如杜塞尔多夫,我觉得它之所以会因为亚洲饮食在小红书上成为网红,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华人觉得可以不用飞回北京或者上海,去杜塞尔多夫就可以吃到这些美食,是一种实用主义的选择;但另一方面,它也提供了一种文化经验,让人们觉得自己被看见了,它肯定了大家的存在感,让这些华人觉得自己不完全是外来者,这里也有属于我们的生活方式,这种体验让社群得以诞生。
至于参与纪录片的拍摄,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这会很有趣,参加这个项目本身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研究,这个项目也为我打开了很多扇门,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我的研究立场。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时代,这导向的是国家之间的对话,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只关心国家层面,那么就有可能把人等同于国家的代表,而不再是人本身,这包含着潜在的危险。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也包括部分的网络空间当中,这种去人性化的叙事是主导性的。但在我的研究当中,我看到的是充满人性和文化的事件的发生,所以我希望通过我的参与,在这个项目中强调各种关系当中富有人性色彩的部分。我觉得身为学者有责任参与公共叙事,尽可能地跟更广大的受众分享这些发现。具体来说,很多人看到的叙事是在杜塞尔多夫有很多中国资本,比如华为、中兴等等,但我想要强调的是,这些在中国企业工作的人,他们也是父亲和母亲,他们的孩子在当地上学,他们想要让孩子尝到家的味道,也想和家人朋友分享自己的文化。他们希望创造一种多元文化的社群,在其中人们可以看见彼此,感受到人情味。我希望展示在贸易、GDP、科技巨头和地缘政治之外,充满活力的中国文化经验也融入在欧洲的日常生活之中。

杜塞尔多夫
澎湃新闻:重访杜塞尔多夫之后有什么新的发现?究竟是谁让它成为了欧洲的“网红”城市?社交媒体用户、算法平台和城市管理者在网红城市的制造中各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Carwyn Morris:刚开始做这项研究的时候,我想知道杜塞尔多夫的中国人是不是在当地复制了中国国内的都市主义。因为拍摄纪录片,我认识了一个网名叫怪素的小红书用户,她在杜塞尔多夫的艺术圈工作,平时也会拍自己的city walk,介绍这座城市和艺术有关的历史。她带我去了一家两个中国艺术家开的艺术空间。我们去拍摄的时候那里正在举办一个为期一周的读书会,主题是非裔艺术家的艺术实践,还邀请了一些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来表演和分享,我们去的那天是一个南美的艺术家在做分享,参与者当中有中国人、德国人(包括少数族裔的德国人)、非洲人、中东人,等等。我没想到会在杜塞尔多夫看到一个这么多元文化的、世界主义的艺术空间。这个艺术空间并不是“中式”的,而是“全球”的。
一座网红城市的诞生必然是很多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在杜塞尔多夫这个案例当中,最重要的还是受众,包括中国留学生、中国商人和中国企业的雇员等等,首先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基础受众群体,他们想要体验生活分享文化,所以会在社交媒体上发跟杜塞尔多夫相关的内容,这些内容吸引别人前来,来的人多了,就有更多的人来投资开店,又产生出更多的内容,受众是这个循环得以完成的基础。小红书的算法和内容呈现方式也很重要,它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线上中文社群。在之前的论文里,我们说网红都市主义是一种都市数字景观,但杜塞尔多夫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景观性其实不是那么强烈,它提供的是一种更微妙的文化体验感,而小红书的算法显然对这类内容给予了支持。杜塞尔多夫的日本移民文化让这个城市对亚洲人而言更亲切,而日本移民社群的衰落又为中国移民的到来打开了空间。当地政府在和日本企业长达60多年的合作当中了解到了亚洲公司需要什么,杜塞尔多夫所在的北威州是德国留学生最多也最为富裕的地区,它对于非欧洲人口,尤其是东亚人的开放程度是没有任何德国城市可以与之相比的。
澎湃新闻:那么,杜塞尔多夫是谁的“网红”城市,当地人知道自己的城市成为了“网红”吗?
Carwyn Morris:当地人可能感受到有一些变化在发生,他们可能也感觉到这个变化跟中国有一些关系,但因为杜塞尔多夫之前就有日韩文化,所以他们可能分不清楚究竟是哪个亚洲国家的文化。虽然可能搞不清楚状况,但还是有很多非中国人参与到新的饮食文化当中。这也和各个社交媒体不同的呈现方式有关,Instagram、Tiktok、小红书像是一个个策展人,通过自己的算法将它们想要呈现的内容推送给用户,小红书攻略式的呈现方式可以让用户更容易地了解到一个城市的方方面面。我有一次在Instagram上刷到过一个美食博主,他在介绍一家在小红书上已经非常火的餐厅时说“这是一个很少人知道的、很有潜力的美食打卡地”……所以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之间,存在着信息差和时间差。通过拍摄这个纪录片,我也希望能让杜塞尔多夫的德国人更了解他们get不到的变化。
澎湃新闻:纪录片中有一个细节,杜塞尔多夫没有唐人街,中餐厅和其他由中国人经营的场所是分散在城市各处的,在这里不同文化之间的区隔似乎被打破了,这种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是一种全球化的理想图景吗?但另一方面,当地的中国人热衷于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生活,有关系紧密的中国人社群,是否又体现出一种全球化的悖论?
Carwyn Morris:我觉得这是更理想的。唐人街的形成是因为最早移民西方的华人受到了很多种族歧视,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来抵抗这种歧视。直到今天,唐人街还是对于中国投资者有着很强的吸引力。比如伦敦现在虽然到处都有中国餐厅,其中也有不少网红店,但很多投资者还是会选择在唐人街附近开店,这种区隔对于一个城市的多元体验是有影响的。杜塞尔多夫的一条街道上,会同时有中国餐厅、德国餐厅、土耳其餐厅、韩国餐厅、日本餐厅开在一起,这其实更像是在中国一线城市会看到的情景,我不会说这是中国城市化的复制,但这确实更接近中国现代的都市风格。
海外的中国人为什么更喜欢用中国的社交媒体,一方面可能是他们觉得其他社交媒体上没有他们想看的内容,或者担心自己不能被很好地理解;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不同的数字空间之间缺乏流动性。在1990年代我开始用网络的时候,玩各种各样的BBS,每个BBS上讨论的话题都不一样,所以要经常在不同的BBS之间跑来跑去,所以对我来说换一个软件,从而看到另一个角度,认识一些新朋友,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可能更习惯呆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不同网络空间之间的断裂是真实存在的,但并不是没有建立联结的可能。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怀着好奇心去不同的平台上看看,虽然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多元文化主义,但如果想要建立一个更开放更友好的社会,这种联结是很有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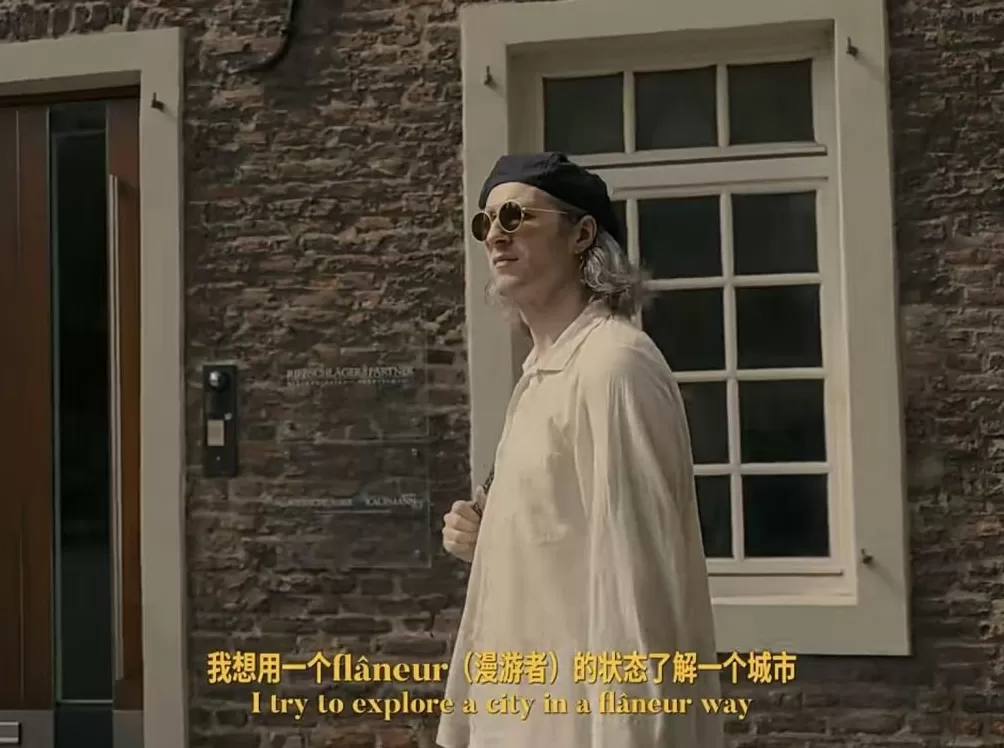
《寻找杜塞尔多夫》剧照
澎湃新闻: 在这部纪录片中,你由当地的小红书博主们带路探访了各种“网红”地标,这种游览方式相比起flâneur描述的漫游,是不是更接近中文语境中的city walk?
Carwyn Morris:我也经常会思考这个问题,从研究立场上来说,研究网络或者说社交媒体与城市的关系,肯定会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些打卡点,需要去现实中的城市里看看它们是不是存在,和网上看到的是不是一样,但与此同时,也要看看城市里有什么,有没有人把它发布到网络上,如果没有人发布可能是因为什么。你需要做一个双重的flâneur,同时在物理城市空间和数字城市空间漫游,要用好奇的状态观察每一条街道,既要在城市里寻找被大多数人忽视的细节,也要在社交平台上查看没人发现没人点赞的帖子。这是一种很有用的研究方法,会让你得到很多原来想不到的经验。但我也没有做得特别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立场。如果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地方,我作为一个英国白人男性和你作为一个亚洲女性,看到的东西和我们的感受可能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读博士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做田野调查,但现在我更希望有一个小组,一起进行一种很随意的city walk,一起观察并不停分享,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探索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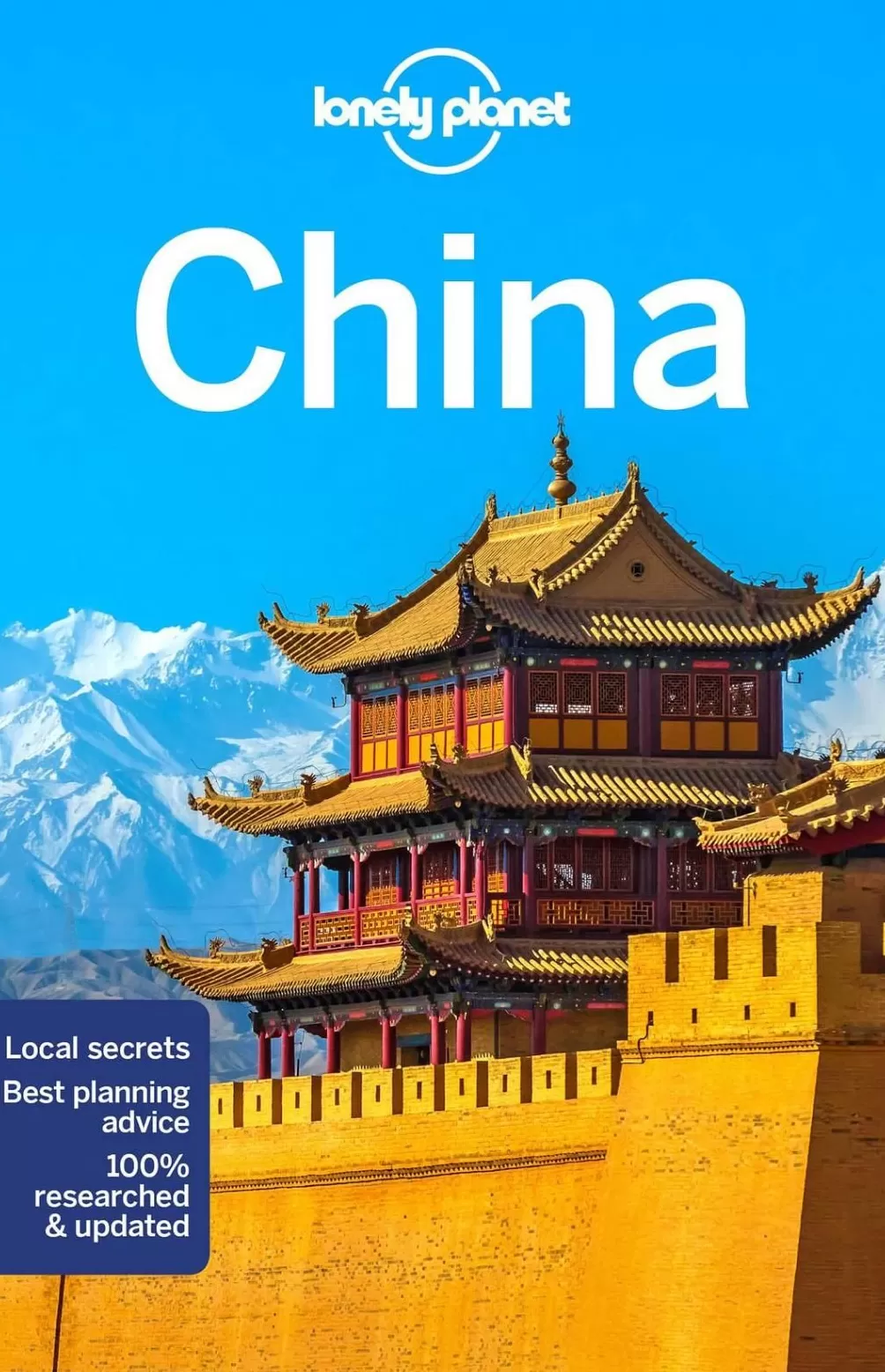
Lonely planet:China(2022)
澎湃新闻: 打卡的旅行方式并不是在社交媒体出现后才开始流行的,网红打卡和过去跟着旅行指南(比如《孤独星球》,《米其林指南》)打卡的旅行方式有什么不同?
Carwyn Morris:我在2005年来中国的时候,住在西安的一家青年旅舍,那里有一本2002年的Lonely planet:China,但我就会想,里面介绍的东西不知道还在不在,也不知道写这些城市旅行指南的人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所写的城市。小红书的用户特别好的地方是,他们一直在撰写关于生活和城市的指南,这和《孤独星球》、《米其林指南》很像,但更与时俱进。虽然我们并不是一直都需要最新的东西,有时候有一个静态的文本是很好的,但大多数情况下,小红书用户提供的更动态、有更多人参与的指南是更好的选择。经常有做旅游研究的朋友问我,去网红打卡点和过去的旅游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受众的参与性是最大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到提供指南的人是谁,可以决定是否信任他对一家餐厅或者一个景点的评价,这是一种更个人化的经验。

重庆网红打卡点李子坝地铁站
澎湃新闻:尽管拥有很多独特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禀赋,杜塞尔多夫原本是一座相对冷门的德国城市,相应的,你在之前的文章中也提到中国的网红城市大多都是二线城市,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尽管有很多网红地标,但不太会被称作网红城市。这是否意味着对于无法跻身一线的城市而言,成为网红城市是一个值得向往的城市身份?
Carwyn Morris:我刚开始研究网红城市的时候也是网红城市刚刚开始受到广泛关注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注意到一个特大城市不太会被赋予网红城市的标签,因为它们已经有一个很突出的城市身份。像上海这个城市,它不仅是一个大都市,也是一个全球性城市。全球性城市的功能是将整个国家和全球经济网络连接起来,允许全球资本由此进出。一个国家的全球性城市也不能太多,中国的一线城市基本上可以说是全球性城市。而中国的二线城市,比如重庆,重庆有3000万人口,英国的人口是接近7000万,也就是说重庆几乎是半个英国,这样一个城市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会是最大的城市,成都、武汉、西安、长沙、南京、杭州……都是这样。但在中国,这些城市无法成为一线城市,那么它们的身份是什么呢?一座城市的居民,他们的身份和城市的身份是相互影响的,他们想要一个更大的、更新的、更现代的城市身份,网红城市一度是一个足够好的新城市身份,目前可能也还是有效的,但我们的城市在不断进化,对于新身份的渴望和追求永远不会停歇。像淄博、天水、曹县这样的小城市而言,它们确实是因为网络才会出名,网红城市对它们而言可能是合适的身份,但对于重庆、成都、西安、长沙等等有趣的、重要的、有影响力的、激动人心的中国城市而言,网红城市只是它们寻找身份的第一阶段,我希望它们可以发明新的城市身份。
中国的城市化旅程的复杂性是无可比拟的,其中的很多问题也是前所未有的,我觉得西方的地理学概念或者城市化理论对于理解中国的城市身份只能提供很有限的帮助。如果想要理解今天的城市,中国是建构21世纪的城市理论最合适的地方。而如果想要理解数字文化,我也会推荐将中国作为研究对象。网红城市就是都市文化和数字文化在当下相遇的一个例子。
澎湃新闻:成为网红城市会如何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或者换一种说法,你会期待自己的家乡或者自己生活的城市成为“网红城市”吗?
Carwyn Morris:我觉得我不会,因为网红本身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我觉得名声本身不是问题,我希望我家乡这个350人的村子有一个网红酒吧或者一个网红餐厅,或者附近有一个网红农场,这会带来一些好处,但如果我的村子有一个网红打卡点,我希望我们可以先好好讨论一下可持续性的问题。
在“网红都市主义”那篇文章里,我们说网红是一种复制的逻辑,但这种逻辑当中包含着一种自我破坏的悖论,因为一旦一个模型被过度复制,它就不再可欲了,受众的感觉会从有趣变成厌恶,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随处可见的“我在某地很想你”路牌。所以如果过度地投资在网红的复制上面,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既是经济上的浪费,也是对资源和可持续性的浪费。在传统媒体的时代,机构扮演了守门人的角色,防止重复的文化产品过度生产;在数字文化的时代,参与都市生活的各方力量和机构都需要好好思考和讨论这个问题,都市数字生活是一个需要治理的公共空间,应该由各个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对我来说,网红研究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我希望理解网红背后的平台、经济和社会。







还木有评论哦,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