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存清代文人笔记及地方志中,涉及“选秀”“选嫔”“采选秀女”的记载可谓“俯拾即是”。近鲁草堂主人所著《养疴客谈》中曾载:
顺治乙酉秋,大兵至。苏州邑中讹言,满州(洲)妇女皆大脚,此来欲选取纤足好女,往北听遣。一时乡村妇女皆去膝衣着草履,以示本质。有俞生者家资殷实,居于东湖。畜(蓄)二丽姬,一曰嫩玉,一曰文鸾,皆妙选也。俞爱之甚,建一阁于湖滨居之,取曹子建赋语,题其阁曰“凌波”。闻讹言令二妾放脚,且使各归母家。迨事过,挈妇已失故步。俞生以为大恨,每对知好言之。一友取滕王阁诗戏之曰:“凌波高阁临湖渚,潄玉文鸾此歌舞。罗袜朝行巫峡云,珠襦暮湿高唐雨。蟾钩脱絓日悠悠,步阔风生裙底秋。阁中屧乡令(今)何在,只合沧浪试浊流。”闻者皆为绝倒。
尽管该则笔记中有多处错讹字,甚至俞生所爱之丽姬者究竟名“嫩玉”还是“潄(漱)玉”,文中前后也不一致,但文中所言苏州一带关于朝廷“欲选取纤足好女,往北听遣”之说却并非一家之言。江南一些府县的地方史志中也曾出现过相类似的记载,如:江苏太仓州璜泾镇曾有“丁亥春讹传选采,民间子女相配不择吉,不计礼,朝议而夕婚,无贵贱靡然,半月配尽,女未蓄发者多出阁,官府谕不听”;上海松江府青浦县亦有“丁亥民间讹传遣中使选秀女事,里中男女无论长幼,嫁取殆尽”之事。志中所记“丁亥”即顺治四年(1647年),与近鲁草堂主人所言“顺治乙酉秋”的时间相隔不远,可以推定“宫选”之说在民间流传应当是确有其事。而且从地方史志与文人笔记对它的描述来看,民众对选秀女流言的反应可谓惶恐尤甚。可以说这是清代初期社会影响最为轰动的流言之一。

《甄嬛传》选秀场景
“造孽太甚矣”:惶惑小民的“宫选讹言”
在各地方的史志中,有关选秀女流言的记载常常被归至“祥异志”之下。这些“宫选讹言”在清朝初期酿成了诸多的人生悲剧,产生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堪称“造孽太甚矣”。
(一)“婚嫁殆尽”
民众听到选秀女流言时最主要、最常见的反应是急于婚嫁。在各府州县的史志中,“婚嫁殆尽”成为描述该流言社会影响时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江西《鄱阳县志》中记载,顺治十一年(1654年)“民间伪言采童女,孀妇婚嫁殆尽”。江苏常州《江阴县志》也载,顺治十三年“民间讹传采绣,数日间男女嫁娶几尽”。同年,扬州府通州境内“讹言采淑女,嫁娶一空”;苏州府嘉定县亦有“哄传选女”;在浙江省嘉兴府桐乡县,“讹言又兴,婚嫁不已”;南康府建昌县亦“讹言选择,婚嫁略尽”;顺治十三年冬天,江西九江府湖口县“讹言宫中拘刷童女,民间嫁娶殆尽”;南昌府武宁县“讹传选妃,男女一时无长幼,婚嫁殆尽”;湖北安陆府《天门县志》也载顺治十三年当地“讹言宫选,如万历壬寅年,婚嫁殆尽”。
至康熙朝,广东惠州府归善县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也出现“讹传取女时,军民惊惶,日夜遣嫁”之说;漳州府海澄县亦有“妄传朝廷点绣女”等传言。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冬,徽州府婺源县“民间有讹言,深山穷谷,嫁娶纷纭,闺阁为之一空”。而直隶保定府祁州则是在雍正五年(1727年)出现了“讹言采选秀女,民间嫁娶若狂”的记载;保定府束鹿县也在当年出现“谣言选淑女,一时讹传满县,民间嫁娶殆尽”之现象。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十二月,浙江湖州府乌程县双林镇讹言选宫女:“先是十一月间有选满洲旗下官员军民幼女之说,并与汉人无涉,一时讹传概行来选。江浙地方民间闺女,不论贫富、良贱,即日婚配。十二月二十三日黄昏,忽传言明日邑令来镇查点,于是鸣锣四出迎娶,灯火盈街,如同白昼。次日,寂然无闻,尚有宰杀猪羊、驰买衣饰者。”尽管很多地方志内对朝廷采选秀女讹言的表述仅有寥寥数语,但这些记载均不约而同地使用“婚嫁殆尽”等语来形容民众听闻流言后的举动,该流言的恶劣影响可见一斑。
(二)“仓惶择婿”
考虑到撰写历史文献需要秉承真实、客观的写作原则,各地史官在编写地方志时对选秀女流言的描绘皆是言简意赅,惜墨如金。相比之下清代文人在笔记杂谈中的描写则是“绘声绘色,不惜笔墨”。在清代浩如烟海的笔记文存中,下层百姓听到选秀女流言之后的过度反应远远不止于“嫁娶纷纭,闺阁为之一空”。各地出现的奇闻逸事完全可以用“荒唐至极”来形容。
在中国的传统礼教之中,儿女婚姻大事讲究“门当户对”,而且程序上“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而在流言的裹挟之下,那些家有千金的父母早已无暇顾及“门当户对”的联姻原则。为了避免待嫁闺阁的女儿被朝廷点选,家长们皆不论门楣慌忙择婿。顺治四年(1647年),松江府青浦县珠里镇“民间讹传遣中使选秀女事,里中男女无论长幼,嫁取殆尽。至有配非其偶者,有人咏张长舆所敬‘马上郎君尚乳臭,鱼轩新妇泣呱呱’句,嫁女者闻之为之酸鼻”。陈鼎《留溪外传》记载徽州府歙县“讹言采宫女于江南,民家女年十三以上者,无不嫁”,当地潘姓人家以“人情皇皇,遍国中无不婚嫁者矣,势难留汝”来劝说自家女儿同意出嫁。
在“仓皇择婿”的氛围之中,还有一些家庭干脆将“媒妁之言”这一必经流程也置于脑后。顺治十四年(1657年)三月,惠州府长乐县“一夜嫁娶殆尽”;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七月,漳州府海澄县“妄传朝廷点绣女,使者即至,无论已聘、未聘,一时民间凡聘而未娶者,皆遣还夫家;其未聘者,仓卒匹配,燕婉戚施,不暇择也”。清代文人董含笔记中记载:“大河南北,以迄两越,无论妍丑,俱于数日中匹偶,鼓乐花灯,喧阗道路。有一婿数家争之,男子往往中道被迫成婚。又有守节颇久,不得已复嫁,亦或借此再适者。”顾公燮也记道,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苏州“有女之家,震恐仓皇,不论门楣,不择佳婿,幸结丝萝,如释重负。有朝问名而夕合声者,有先缔姻而急迎归者”。姚廷遴形容:“父母着急,不论贫富,将就成亲,遍地皆然,真亘古未闻事。”
(三)“不计礼仪”
在急于嫁娶的心态之下,许多人家在婚聘嫁娶时根本无暇顾及传统的礼俗规矩。《内丘县志》记道:“凡家有女子者,不论门第,亦不问年庚,或定于杯酒,或约于一言,或童首而戴髻,或暮夜而误送。香楮舆马,价涌十倍。”姚廷遴《历年记》也载:“夏间讹传朝廷采选秀女,府县城镇乡村僻壤,有女在家者俱惊惶无措。早说暮成,俱幼婚配;不必三杯水酒,只用一鼓一笛;甚至良贱不拘,岂论贫富难匹。限时限刻,从早至暮,从暮达旦,无论日之吉与不吉,周堂利与不利,遍地结亲,亦希遇之事。”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时,当地的恐慌更甚:“迎亲并亲日夜不停。并亲者着忙之甚,百物皆贵,甚至不论贫富,不计礼仪,以不择门当户对。不管男女年纪大小,大约茶二斤礼银四两为最,更有不费分文者。”
即便还有人家坚持沿袭多年的礼俗,但从婚聘场面的描述文字来看,这些婚礼操办得也非常草率。据吴江士人袁栋之《书隐丛说》所记,当地“成婚之际,礼节苟略。乐部仅一二人,且有粗晓吹笛、打鼓以漫应之者;舆轿不足,有以红布围于倒桌以舁新人者,致可笑也”。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也描述,当地“鼓乐之声昼夜不绝,一时彩缎等物价高十倍,执事人役分身奔走不遑,或伪称受聘而以糕果分途亲邻,计图脱免,此亦姻缘一大劫也”。上海《紫堤村小志》亦记载当地“近苦罕肩舆,率倒桌向上,竿竹围帘,舁成嘉礼。阡陌往来,自朝彻暮不绝。凡一乐人受酬,横被拖拽,一日夕可数十家,腹枵声哑,亦有并此不用者”。至乾隆朝,这样的情况再度上演。乾隆十七年(1752年),湖南长沙府府安化县“民间讹言选妃,富者赘婿,贫者送女,皆不及备礼。讹息,有索礼致讼者”。
(四)“终身之悔”
在仓促婚嫁之下,各地“贵贱不等,老幼不齐”的婚配情况可谓比比皆是。更有甚者还趁机“匿情再娶”,因而也酿成不少“茍且于目前,而贻悔于终身”的悲剧。例如:陆文衡在《啬庵随笔》中载“民间女子数日之内,婚嫁略尽,仓卒成礼。其老幼相悬,贵贱不伦者颇多,致有终身失所之悔”;陕西《凤翔县志》中亦有“民间讹言大婚,嫁长幼多至失伦”之说。在浙江钱塘县,有“余同里武进士陈大生之女,与儒者沈子昇如虽有盟言,实未聘也。……幼时婉娴端淑,素有烈志。丙辰岁,民间讹言选宫,一时嫁娶若狂。沈子因媒妁言,遂问名焉。时贞女年已十九矣。……沈子又浪迹天涯,姻盟之事略未齿及,竟欲付之流水,女微闻此意,其心尽神伤,终宵饮泣”。顺治十五年(1658年),广陵(扬州)“有老儒孪生二女,有姿色,俱好文墨,并处不能辨长幼,以香炙面为识。是秋讹传掖廷之选,仓卒归二少年,嫁同日,娠同时,死亦病,病亦一”。洞庭湖以南的长沙府浏阳县亦有“讹言宫选,邑骚动,民间至有童男女漏夜成婚者”。褚人获在《坚瓠集》中记苏州府长洲县“邑中愚民,纷然嫁娶,花轿盈街,鼓吹聒耳。……今事成俄顷,不无以倾城之貌,而误适匪类”。人心惶恐之下真人版“嫁错郞”的闹剧也是频频上演,“有张家妇而误抬至李家者,有李家女而误至张家娶者”,直隶广平府曲周县志中亦有“有送女夫家,误致邻室,至于相讼者”。
因选秀女流言而酿成的以女性生命为代价的人生悲剧更令人闻之痛心。在一些地方志关于“烈女”的记载中,就有不少因流言而致“抱恨自裁”之例。扬州府泰州安丰亭百姓王北望,因家境贫寒,误信媒婆之言,将女儿许聘某富家子。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冬天,“民间讹言朝使且至,将采宫人于东南吴越间,民家女无论妍媸,父母不暇择配,多遣嫁。已聘者,迎归。于是所约者亦昏期来。女知之,私问其弟曰:门外水能溺人乎?弟幼无所知,乃实告曰水浅,惟某处河溺则不复生也。抵夕,女故作欢容北望,妻以女且喜不深疑,女乘间缝衣裳甚固,投弟所指水深处死。”嘉兴府秀水县庠生沈琛之女,二岁时许配姚徽之子姚正宗。姚正宗十四岁夭亡,沈氏誓不再嫁。至二十六岁,“民间讹传宫中点选,父惶惑,欲更缔姻,氏忧忿卒”。苏州府太仓州沙溪里节妇龚淑真因听闻嫠妇送采女之伪言,“惧不免,纫衣带,投后园泽中,水为之沸。园妪大惊,呼群婢挟之出,得不死”。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四月广东惠州府归善县“讹传取女,时军民惊惶,日夜遣嫁,即十余龄处子,遽尔有家;惑及孀守之妇,多有自尽全节者”。康熙三十二年,长洲县“讹言选民间女入宫,命嫠妇率以行。时吴地一二百里内,婚嫁几尽”;甫里镇节妇钱氏“密以利刃自随,其从女见而问,故曰吾旦夕或需此”;苏州府嘉定县也有“民间配合失伦,事后有抱恨自裁者”。清代文人陆文衡在《啬庵随笔》中用“造孽亦太甚矣”来形容选秀女流言所酿成的人间悲剧。
“传播说非一”:引发恐慌的纷纭众说
“选秀女制度是清代最具满族特色的制度之一,也是清代宫廷得以建构的重要基础。”清代秀女选拔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皇帝及皇室王公遴选后妃和妻妾,由户部负责从八旗女子中选拔,每三年举行一次;另一类是“每岁选内务府属旗秀女”,即从正黄、镶黄、正白内务府包衣三旗的女子中为皇宫挑选“承值内廷”的宫女,由内务府负责,每年举行一次。也就是说,清代只有旗籍人家的女儿才有资格参加秀女选拔,普通人家的汉族女子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宫廷。因此当时曾有人讽刺道:“独不思里巷之女,有何德何貌,可以充贵人之选也?”尽管有学者认为江南民众面对选秀女流言的过度反应是庸人自扰之下的“愚之甚矣”之举,但如果将文人笔记与地方史志的这些记载置于当时的社会情境中去观察,可以发现“造孽太甚”的选秀女之说能够如此轰动,其实有很强的现实因素。它的流行也折射出下层民众对东北少数民族新政权的复杂心态。
(一)充掖宫廷
在选秀女流言的诸多版本中,朝廷采选民间女子送至宫廷充当宫女是最能挑动公众敏感,引发百姓恐慌的说法。汉中府南郑县士人宋师濂《忧旱有感》云:“火云燎绕赤轮悬,尘起梁州万井烟。术士通衢犹卖雨,农夫乡里已无年。忽传选秀充宫嫔,又说登髦补宦官。婚嫁横添劳攘事,何堪边鼓更喧阗。”河南府嵩县士人傅而师《选女》诗云:“使者初颁燕地诏,传言次第下周秦。吴越远人引领望,欣逢天子结朱陈。官道鸾车日夜驰,调筝调瑟奉盘匜。君王忽厌红妆好,更有新传选少儿。”
从当时文人笔记的内容来看,流言中关于选嫔妃、选宫女的细节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顺治初期,民间所流传的选女标准多为“殊色女子”或“好女”,如苏州府吴江县人陆文衡记载:“(顺治)丙申七月,有旨在京各府选择东西二宫,吴下好事者讹言,将遍选各省殊色女子,江南美丽尤多,将倍选焉。”
近鲁草堂主人的笔记《养疴客谈》记载,在顺治二年(1645年),苏州境内广布之流言是“满州(洲)妇女皆大脚,此来欲选取纤足好女,往北听遣”。然而至顺治朝末期,选秀的范围已不局限于“好女”,如蒲松龄在日记中提到顺治十二年(1655年)山东济南府境内的选秀女流言是“将选良家子充掖庭”。据描述当时济南府“人情汹动,刘公初不信,而意不敢坚,亦从众送女诣婿家。时年十三,姑董与同寝处。讹言既息,始移归”。顺治十三年七月间,扬州府泰州所流传的版本也是“讹传选宫女,民间婚配惟恐后,室女为一空”。而《内丘县志》中也载“顺治十三年,有选嫔之举,人皆惊惧无措”。
事实上朝廷对这则流言也有所耳闻。顺治十二年七月三日(1655年8月4日),兵科右给事中季开生向顺治帝上疏:“近日臣之家人自通州来,遇见吏部郎中张九徵回籍,其船几被使者封去。据称奉旨往扬州买女子。夫发银买女,较之采选淑女,自是不同。但恐奉使者不能仰体宸衷,借端强买,小民无知,未免惊慌,必将有嫁娶非时,骨肉拆离之惨。且乘机而奸棍挟仇捏报,官牙垄利那移,诸弊断不能无矣!……皇上上体祖宗之寄托甚重,下念兵民之心力甚劳,鉴臣蚁衷速收回成命,则宵旰之勤益专,江海之氛必靖,亿万年享久安长治之福矣。”然而这封奏疏却惹恼了顺治帝。据《清实录》记载,顺治帝专门颁发谕旨对此事作出回应:“前内官监具奏乾清宫告成在即,需用陈设器皿等项,合往南省买办,故令发库银遣人往买,初无买女子之事。”
顺治帝强调:“太祖、太宗制度,宫中从无汉女,且朕素奉皇太后慈训,岂敢妄行?即天下太平之后尚且不为,何况今日。朕虽不德,每思效法贤圣之主,朝夕焦劳,屡次下诏求言上书,禁勿称圣,惟恐所行有失。若买女子入宫,成何如主耶?”紧接着,顺治帝在谕旨中严厉斥责道:“季开生身为言官,果忠心为主,当言国家正务实事,何得以家人所闻,茫无的据之事,不行确访,辄妄捏渎奏,肆诬沽直,甚属可恶,着革职,从重议罪具奏!”最终,季开生因“妄听讹言,渎奏沽名”被刑部处流徙尚阳堡。
(二)满汉联姻
清廷在刚刚定鼎之际,曾专门出台过一些鼓励满汉联姻的政策以化解民众中的民族对立情绪。1648年10月6日,顺治帝传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不久,顺治帝又于14日再谕:“朕欲满汉官民共相辑睦,令其互结婚姻,前已有旨。嗣后凡满洲官员之女,欲与汉人为婚者,先须呈明尔部,查其应具奏者即与具奏,应自理者即行自理。其无职人等之女,部册有名者令各牛录、章京报部方嫁,无名者听各牛录、章京自行遣嫁。至汉官之女欲与满洲为婚者,亦行报部。无职者听其自便,不必报部。其满洲官民娶汉人之女实系为妻者,方准其娶。”
朝廷在一月之内连发两道谕旨鼓励满汉联姻,但是这个新建立的满族政权在汉族民众中面临着巨大的信任隔阂。清宗室昭梿曾记道:“本朝定例,从不拣择天下女子,惟八旗秀女,三年一选,择其幽娴贞静者入后宫,及配近支宗室,其余者任其自相匹配。”虽然按照清朝的制度,只有旗人女子才有资格入宫,也就是说皇室采选秀女与普通的汉人并无瓜葛,不过江南民众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因为满族达官贵人掠夺汉族女子之事在清初亦不胜枚举。这也加剧了民众对朝廷鼓励满汉联姻的过度猜忌。顺治五年(1648年),上海松江地区出现“婚配者更甚于前,其时大为惊惶”的情况,就是因为民众曲解“朝廷将关外并满州(洲)女子,驱逐而南,配与中国男子,天下一家,华夷为眷”。顺治十年(1653年),上海再度“哄闻满州(洲)之女发配中国男子。中国女子要配满州(洲)男子,名曰‘满汉联姻’”。
(三)馈送西虏
除了选女入宫、满汉联姻外,还有民众担心清廷以采选宫女为名,将汉族女子作为讨好西虏的牺牲品。这种说法见于叶绍袁《启祯记闻录》。顺治四年(1647年),“民间竟传北来有旨,欲选少艾之女,以馈西虏,人心惶惶。四月下旬及五月初旬,争先嫁娶。肩舆、乐人、掌礼、厨司等,价高数倍。鼓吹接踵于路。按抚及有司出示晓谕,至月中方止”。尽管叶绍袁在文末以“大属可笑”来评价时人对采选宫女之说的过度反应,但从一些方志的记载来看,这种说法在江南一些州县极为普遍。如浙江杭州府海宁县就有“讹言采妇女犒西鞑,一时嫁娶殆尽”,浙江嘉兴府桐乡县也有“讹言选西女,民大骇,亟配合,嫠妇嫁且尽”。馈送西虏说在江、浙一带持续流传一月有余,百姓在流言裹挟之下惶恐异常,甚至惊动了巡按等高阶官衙专门出示晓谕以安定民心。顺治十四年(1657年),广东岭东兵备道李文煌在其所辖惠州、潮州二府出示《为严禁讹言惑众以安地方事》一文:
照得我朝定鼎,法制修明,无一举而非仁民爱物之心,无一行而非保民致治之事。粤东界在南服,去京师辽远,有等不法奸徒,惯倡异论,摇惑地方。兹又访得前项奸徒创言流布,有选取幼女、寡妇,充为宫使,以给蒙古之说。致使里巷愚民承讹踵谬,各将贤淑幼女,混嫁非偶之徒,三从罔顾,六礼不行。且有守节多年之婺妇忽抱琵琶,从戎未返之征妻顿乖琴瑟,伤风败俗,坏法乱伦,莫此为甚。
文末李文煌还严词警告:“尔等从前所听,尽属讹言,毫无影响。自示以后,各宜安心乐业,无得轻举妄动,以致伦理乖张,男妇失所。如有云云,许捕巡员役及地方人等密访得实,或禀该地方官,或即具呈本道,以便严拿嫁娶之家,并媒妁人等,立置重法,决不姑贷。”
然而地方官员的告示没有打消民众心中的疑虑。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春,广东一马姓官员之女被皇上纳为妃,立即引来两广地区民众蛇影杯弓的猜忌,不久便出现“两广总督吴兴祚要选取选良家女十六人随嫁”之说,之后还演化出“朝廷要选淑女充后宫,又说西虏进贡,要回赐好女子千余”等其他版本;潮州府揭阳县也出现“民间讹传欲取室女为边兵妻,室人家纷纷嫁娶”之现象。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北京城又出现“挑选秀女赐西洋人”的讹传。为此雍正帝专门颁布上谕做出澄清:“近有不法匪类,造作讹言,一人煽惑,众口喧腾,以致人心惊惶,良民受累。如京城之讹传挑选秀女赐西洋人,浙江之讹传海宁屠城。”他将此归咎为“奸恶之人”作祟,这些人“不肯改过迁善,怨朕约束惩治甚严,故肆其鬼蜮之伎俩,以摇惑众心”。雍正帝厉声警告:“朕非庸懦无能主也。如京城造言之人,现在拿获,按律治罪……奸恶之人,愍不畏死,谤国害民,法所不宥。嗣后该地方有司,务期密访严拿,立置重典。凡尔远近良民,当共信朕断不肯为累民之事。一切浮言,彼此相戒勿听,则俯仰顺适,寤寐安舒,永无仓皇失所之虑,庶不负朕勤民保赤之心,而奸恶不法之辈亦无所逞其伎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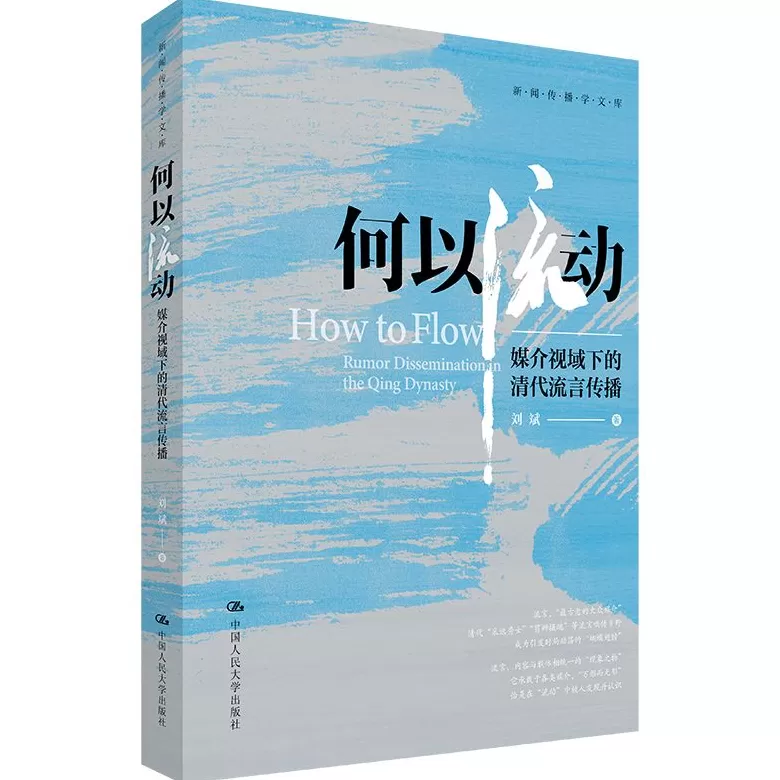
(本文摘自刘斌著《何以流动:媒介视域下的清代流言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10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还木有评论哦,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