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采尔在1897年出版了《政治地理学》,两年后契伦提出“地缘政治”(德文Geopolitik)的概念,标志着地缘政治学的正式诞生。地缘政治学诞生至今已经一个多世纪了。清季民初,地缘政治学理论传入我国,对我国传统地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为《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即颇受西方地缘政治学思想之影响。其时当国家危难之际,政治地理一经传入,即掀起热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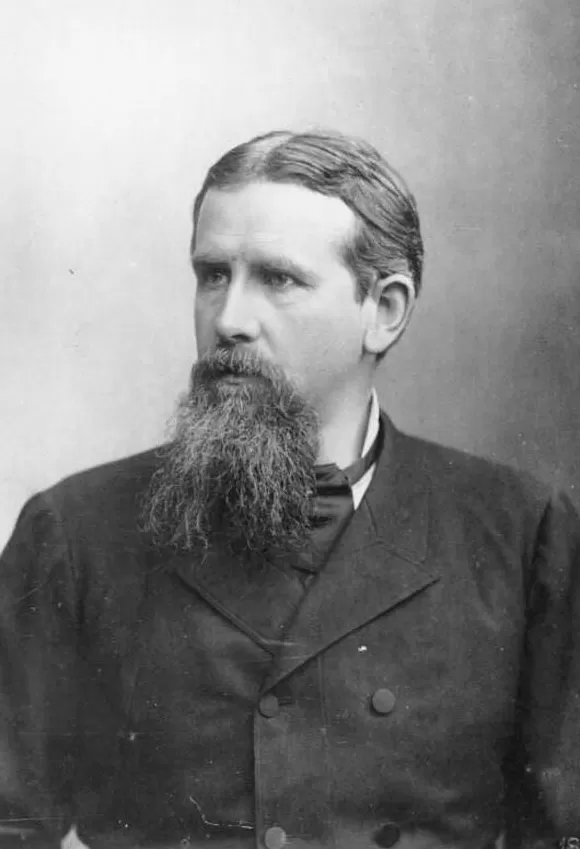
弗里德里希·拉采尔(1844-1904),德国地理学家
二战后,由于卡尔·豪斯霍费尔的地缘政治理论间接成为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而臭名昭著,各国学者视“地缘政治学”一词为过街老鼠而避之不及。我国对于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后方才开始打破对这一领域的禁忌,到21世纪开始以前尚停留在对于西方地缘理论思想的介绍和初步研究阶段,而从地缘政治学视角来观察中国历史更是寥寥无几。但是近十年来,地缘政治学研究日渐活跃,以国际关系学、历史地理学、军事学为主体的学者对于地缘政治的内涵、研究对象、地缘规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一些学者开始用地缘政治的方法来具体探讨中国历史上的地缘实践规律,具体分析中国古代的地缘思想。但是,从国外学者的研究情况看,则较国内起步要早,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用地缘政治学的思想研究中国的边疆形态与王朝演进规律。王恩涌先生在谈到政治地理学的性质时首先即谈到其“历史性”,他指出:“和其他许多学科相同,政治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性质就是它的历史性或时代性。”回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去探讨特定时期的时空政治格局和实践规律是件很有学术意义的事情,而这个工作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更为迫切。地缘政治学本身即是关乎国家安全的学问,洞悉中国古代王朝的地缘实现之路,了解其规律和经验教训,对于巩固国土防御、制定合理的国家战略意义重大。
我国古代虽未有明确的地缘政治概念,但是地缘实践的渊源却极为遥远,不但地缘实践丰富多彩,地缘思想也有着鲜明的中国特点。这不仅为中国学者所重视,也为西方地缘政治学者所注意。除了拉铁摩尔外,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了中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系统之内的地缘核心区的规律及其地缘政治的特性。论及东汉以前之中国地理大势,傅斯年先生曰:“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对于周代的封建制与宗法制相结合的特殊制度,周振鹤先生深刻指出:“封建制是地缘关系,宗法制是血缘关系,封建制与宗法制二而一,一而二。这是以地缘关系来维护血缘关系。”“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成为西周独特的地缘景观。
从西周具体的地缘格局来看,首先即营造洛邑,利用殷商遗民以摄制东方,这便形成了渭河平原与伊洛平原的首次地缘结合,其后封周公于鲁、姜尚于齐,与洛邑直接相呼应,这大抵乃横向地缘轴线的远绪。对于伊洛平原之于关中的地缘重要性,傅斯年先生谓之:“又其次是伊洛区,这片高地方本不大,不过是关中河东的东面大口,自西而东的势力,总要以洛阳为控制东平原区的第一步重镇。”对于周人平定管、蔡之乱的二次分封,钱穆先生指出:“鲁、齐诸国皆伸展东移,镐京与鲁曲阜,譬如一椭圆之两极端,洛邑与宋则是其两中心。周人从东北、东南张其两长臂,抱殷宋于肘腋间,这是西周的一个立国形势,而封建大业即于此完成。”当西周立国伊始,王畿据有渭河平原,向东以伊洛平原作为东向伸展,齐、鲁遥相呼应以遥控大平原之形势,并以晋、郑等姬姓诸侯国为枝辅,立国气势可谓宏远。而在南方,周人继承了商人对于南疆的经略,以南阳为中心建立起南控荆蛮、东驭淮夷的地缘格局。总体言之,西周以洛邑为中心构建了“十字形”架构的地缘政治结构:横向地轴为宗周-成周-齐、鲁一线,宗周为根本所在,成周为控驭东部之大本营,而齐、鲁则为其前哨,于地轴之两侧诸多封国呈放射形展开,北及幽燕,南达江淮;从纵向观察亦有一隐形之轴线,其北依太行、南连南阳,前锋则直指荆楚核心的江汉平原,东出则势关淮水。从根本上看,西周坐守关中而东向进取,依托众多的封国而开辟了以西驭东的地缘模式,从这种意味上看,北至幽燕,南至淮水都是广义上的东方,唯独南阳、江汉一带算是自洛邑而南的一个延长线。这大抵是西周立国的基本地缘构架所在。
然则犬戎来犯,平王东迁至洛邑后,则形势大变,伊洛平原的根在于关中,东迁后渭河平原拱手让与秦人,郑、晋诸国环伺,根本已失,国势陡降。大平原上形势自成一体的齐国率先称霸;昔日藩辅关中的晋国势力日渐伸展,亦为一霸;秦人锐意经营关中,渐成一偏霸。此三者构成了北中国的地缘主体。而南疆之楚则最为大国。历数春秋五霸则会惊异地发现,其中齐、秦、楚、晋四国恰好位于西周立国的纵横地轴之上,是以司马迁感慨而曰:“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在太史公眼里,四国的崛起与西周地缘轴线之地理优势关联甚密。而大国之尤者之晋、楚二国则处于纵向地轴之上,春秋大部分的历史即是晋、楚争霸的历史。从这种意味上说,春秋的地缘政治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纵向地轴转动的历史。
当战国之世,血缘之纽带荡然无存,各国皆务于地利与地力之获取,开疆拓土是为第一要务。从东向观之,齐国在大平原上的地位极为独特,徐州相王,魏国尊其为王;齐、秦互帝,亦在此横向轴线之上;在连横策略上,齐、秦二国也为其发起的重心所在。北向地轴之晋国一分为三,战国初年,三晋之尤者魏国疆域关联太行之东西,其因在战略上首鼠两端而终于被秦人逐出河西,自此秦人解除了东疆之威胁。秦惠文王时期南向灭巴蜀而实现了渭河平原与成都平原的地缘联合,从而开辟了新的地缘轴线。秦昭襄王时期又北逐义渠而筑长城,自兹始秦人的纵向新地轴初步奠定。新地轴尤其是秦蜀地缘联合体大大加强了秦国的地缘力量,秦人借此而强化了对于旧地轴的冲击力度。而在南向,随着秦人占据巴蜀而渐次将楚人的势力逐出,楚国的西疆门户洞开。伴随着旧地轴的日渐破碎与楚国遭受的地缘压迫,东方列国彼此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残酷。是以秦人开启的纵向新地轴乃是其席卷天下进而完成一统的关键步骤。

万全长城卫所博物馆内用沙盘模型展示的“野狐岭”长城沿线军事防御体系。视觉中国 图
伴随着秦国最终统一六国,新旧地轴实现了历史性的合璧,而随着蒙恬的北逐匈奴,纵向地轴得以延伸到阴山一线,北向地轴实现了空前的形势完固。秦人以关中而取天下,随着新旧地轴的合璧,秦人理所当然地将大关中视为帝国控驭的根本所在。但是,秦朝建立后地缘活动着力于南北二端从而导致了战略上的中空局面,加之其不恤民力而用法残暴,始皇没后,陈胜振臂而天下蜂起,秦帝国的地缘体系迅速土崩瓦解。
秦汉之际,项羽恃战胜之威而主导列国,在项氏的大分封中,对于东西地轴的齐、秦二地皆将其一分为三而予以肢解,同时将刘邦势力分封于巴蜀,力图暂且冻结刘邦势力,待到戡定东方之后再行解决。由于斯时东方未宁,项羽定都的彭城亦位于东向地轴之上,以便随时预于形势,然则当齐地崛起于彭城之侧,旧地轴之上的赵国亦日渐坐大,刘邦东出而再度夺取关中,而自韩信一举摧毁了根本于旧地轴之上的赵国,天下形势向着刘邦急剧倾斜,项羽亦终于在数线作战的窘境中走向灭亡。东向地轴之意义在秦汉之际表现得尤为明显,韩信始定三齐,刘邦即入壁夺其军,旋即迁韩入楚,然则斯时韩信之楚国所在之地亦含有淮北、淮南一部的广大地域而势关齐、鲁,是以韩信入楚未暇刘邦即执之入京始后安。斯时,田肯贺刘邦曰:“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执戟百万;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此东西地缘轴线的意义亦为严耕望先生所显见:“观此,则当时立国形势,与初封异姓功臣者无异。所不同者,齐地本由汉朝直接控制,今以封长庶子耳。齐王肥于诸王中最为亲近,故以不封他人之齐地予之。……高祖不但以亲生庶长子为齐王,且以直系部队中军功最高之功臣曹参为之相,统重兵,驻齐国,北与高祖会定陈豨,南与高祖会定黥布。及汉相萧何卒,而曹参为当然继承人。可知当时实视齐为东方支柱,镇抚东土,仍与长安为东西横轴之两端。其立国形势,盖与西周封鲁相类矣。”
从项羽到刘邦,斯时对于定都问题的反复讨论亦足可见关中模式对于时人的深刻影响。而关中模式首先从秦人据有汉中与蜀地进而打开东进局面开始,后刘邦也正是由蜀地而关中而东向夺天下,再次演绎了这种模式。自从秦始皇夺取河南地以后,河套地区对于关中的地缘意义也日益彰显,从时人的观念可以见其一斑,战国时人言及关中形胜皆谓之以“被山带渭”,而秦人一统后,皆谓之“被山带河”,从“渭”到“河”虽一字之别,但其中的地缘意味极为深远。河套的得失在秦时似乎显得不怎么重要,但是当西汉立国之始而匈奴频繁来袭之际,则足见其对于关中政权的地缘意义。刘邦最终定都关中乃是由于其“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的独特地缘战略地位,但是这种地位随着冒顿统一匈奴而被打破。
西汉初年,不仅要面对东向的王国问题,还要在北部漫长的国境线上面临强大而统一的匈奴帝国的地缘冲击,战略压力极大。这种情势乃是西汉初年实行对匈奴妥协的和亲政策的地缘政治背景。这一政策所造就的相对和平的地缘环境为汉初诸帝不失时机地解决东向的王国问题提供了宝贵时间。西汉初年,刘邦在夺取天下之后马不旋踵次第翦灭了异姓诸王。刘邦一则为惩秦孤立之败的教训,二则鉴于当时军功侯势力强大之现状,开始大封同姓诸王,并确立了“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原则,假血缘之纽带以实现地缘控制成为汉初地缘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而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可谓挢枉过其正矣。”这种局面很快随着血缘的日渐淡化而成为汉廷的潜在威胁。文帝时期利用诸侯国无后、有罪及诸侯王去世等机会而实行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策,剖分齐国为六、淮南为三,而与此同时强化对皇子的分封,实行“以亲制疏、以近制远”的策略,从而将王国问题的解决向前推进了一步。文帝的种种处置使横向地轴呈现出重心逐步西移的趋势。景帝时期在文帝的基础上厉行削藩而终于激起了七国之乱,景帝挟战胜之威一方面进一步削夺王国支郡,另一方面从制度上收回王国的事权,从而将王国问题的解决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随着景帝削夺王国支郡举措的展开,东向地轴日渐呈现出虚无化的倾向。
武帝时期,在元朔二年(前127)的河南之战重新夺取了河南地而实现了纵向地轴的再次完固;在南向则以巴蜀为中心实现了在西南夷地区的地缘拓展,而这一拓展在东南向则有着控驭南越的地缘意义,在西南向则尝试着打通大夏之道的地缘努力,二者皆大大丰富了巴蜀地区的地缘政治内涵。为了进一步强化关中在帝国地缘政治体系中的控驭地位,武帝在元鼎三年(前114)实行了广关的举措,大关中的地缘格局进一步强化。伴随着汉廷在元狩二年(前121)河西之战与元狩四年漠北之战的胜利,在汉军的持续打击之下,匈奴的战略重心日渐西移。为实现彻底战胜匈奴的战略目的,汉廷推行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经略河西与经略西域也应运而生。
这一战略在演进的过程中使曾经因大关中格局的形成而消弭于其中的西向地轴实现了历史性的延拓。在东向,随着推恩令的实行,东向地轴进一步呈现出虚无化的倾向。在纵向地轴之东部疆域,于东北疆定朝鲜而置四郡,于南疆则收两越而置九郡,皆是蔚为壮观的地缘新拓展。汉廷在东北疆的地缘实践乃是对匈奴地缘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放在汉匈对抗的大地缘政治格局之下,斯时东疆之地缘活动的意义则在其次。在基本的“十字形”骨架之外,东南地区由于形势自任且自然条件优越、民风强悍,一直以来是轴线格局之外的一个异数。早在先秦时期即出现了足以震动斯时地缘格局的吴、越等强国;而在帝国时期,东南地区及其相近地区的力量最终得以推翻强大的秦帝国;在西汉时期,吴、楚二国乃七国之乱中之翘楚,淮南屡次叛乱,闽越地区亦是一大顽强势力。凡此种种足见东南地区的地缘能量,这也是东南地区成为关中政权地缘隐忧的原因。这种现象甚至在观念上形成了所谓“东南有天子气”的意识。
凡此林林总总大抵为西周至西汉时期的地缘政治结构演变之大概。秦汉时期乃是中华早期帝国熔铸的重要时期,秦汉帝国的构建脱胎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地缘政治竞争,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地缘政治则发端于西周独特的寓地缘于血缘的宏伟构建,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系统梳理西周以来的地缘政治变迁,并力图从中探索些许规律性的原则,或许对于认识早期帝国的构建与熔铸有所助益。
本文为《帝国的骨架:先秦、秦汉地缘政治结构变迁大势》一书的绪论部分,有删节,注释从略,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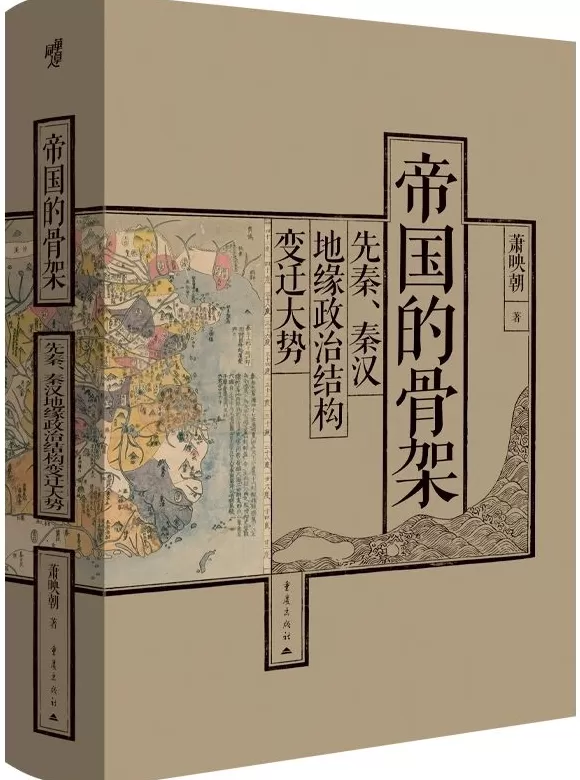
《帝国的骨架:先秦、秦汉地缘政治结构变迁大势》,萧映朝/著,重庆出版社,2025年8月版







还木有评论哦,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