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经作者授权,译自永田大辅、近藤和都编著《使用杂志的媒介社会学:让文化成为可能的“创意”》(雑誌利用のメディア社会学: 文化を可能にする「工夫」)、ナカニシヤ出版 、202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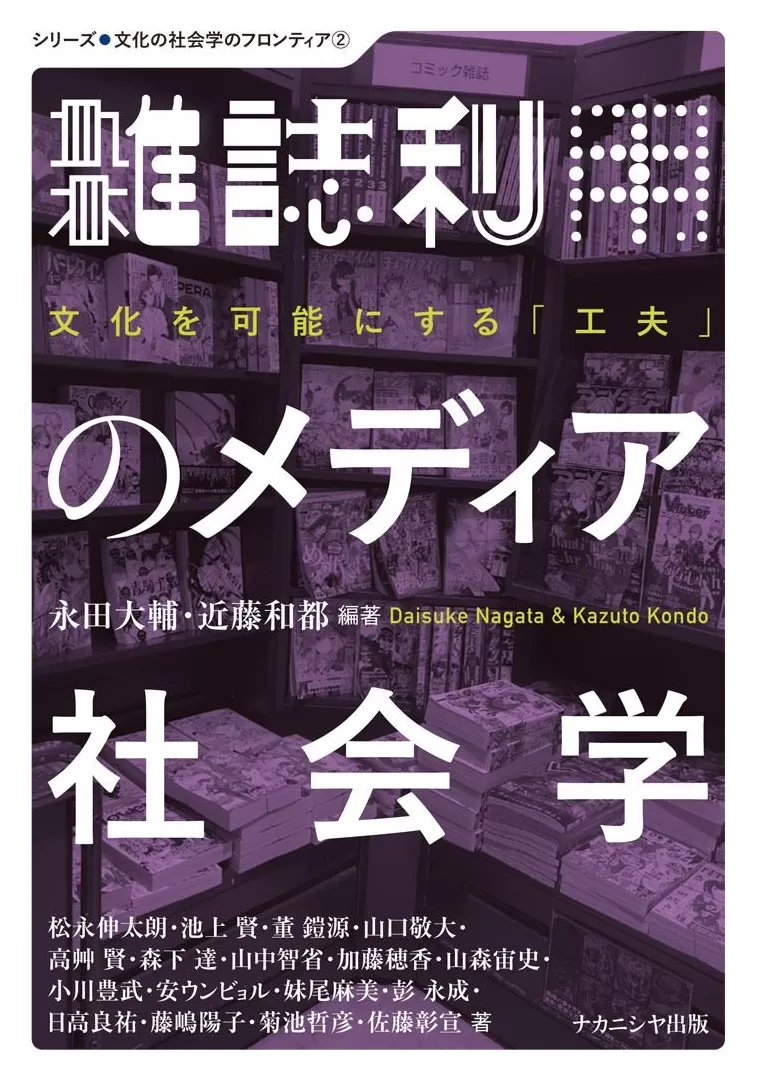
《使用杂志的媒介社会学:让文化成为可能的“创意”》(雑誌利用のメディア社会学: 文化を可能にする「工夫)、ナカニシヤ出版 、2025年。
1.作为一种文化技艺的清单
“清单(包括目录、索引、条目)”指的是将一系列元素或项目按照一定顺序进行编排的记录形式,常见的有购物清单、音乐榜单等等,类似这样的存在如今已经广泛渗透到了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在浏览视频发布网站上提供的海量视频内容时,为了方便日后查找,我们可以将其中感兴趣的内容添加到“收藏夹列表”中。或者也可以一边对照杂志上的“必看清单”,一边在搜索框中输入名称。这类“清单”具有多种功能,比如辅助记忆、排序、表达个人品味以及直观地展现文化鉴赏所需的积累量等等。本文的研究目的便是探讨“清单”这样的存在是如何改变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录像带普及前人们的动画体验。
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掀起了一股动画热潮,与此同时也涌现出了大量的动画杂志。甚至有人认为“动画热潮无非就是动画杂志热潮”(冈田1996:20)。这些杂志刊登的内容中包含了各式各样的“清单”,原本如流水一般、播完便不见踪影的动画相关信息就这样以“清单”的形式被储存了下来,使得人们可以将这些信息分享给彼此并反复查阅。上文提到过“清单”具备多种媒介功能,这也就意味着“清单”的出现势必会带来一些前所未有的动画体验。因此,接下来本文将以拥有广泛读者群并且至今仍在发行的《Animage》(1978年创刊)为研究对象展开讨论,重点探讨“清单”这种信息形式与动画体验之间的关系。
与文本或图像这种具有分析解读价值的信息呈现形式不同,“清单”具有一种使信息可视化的结构,所以它跟言语不同,并不具备“阅读”的可能,因此往往被视为补充前者的次要事物。但是,就像佐藤健二(2015)在谈到“索引”时指出的那样,虽然“索引”经常会被看作正文的补充项目,但实际上正是因为“索引”的存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章的主旨和要点,一个完整的文本才能最终得以成形。这表明阅读和写作并不是单纯的文本活动,而是一种由多种形式共同支撑的实践。因此,“清单”并不是什么“次要补充”,而是一种重要的技术——通过其自身特有的形式,帮助构建结构化知识体系的独特技术。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本文将主要借鉴丽莎·吉特尔曼(Lisa Gitelman)提出的批判性视角:她认为用“印刷文化”这一笼统的范畴去探讨事物会忽略掉围绕阅读与书写产生的各种历史实践(Gitelman 2014)。吉特尔曼引用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的“紧缩策略(Deflation Strategy)”(Latour 1990)——即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微不足道的事物和实践实际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进而强调在媒介史的研究中,我们应该重视“文档”这种不能被归入文学或书籍范畴的形式的重要性。所以,本文没有选择那些历来就备受重视的事物作为关注点,而是将目光聚焦于长期遭人忽视、从未被深入探究的“清单”,探讨它所具有的媒介功能。
另外,也可以把“清单”视为一种“文化技艺”。伯恩哈德·西格尔特(Bernhard Siegert)认为,“文化技艺”这一概念是在与两种传统研究路径的对抗中逐步发展成熟的:一种是主要从大众媒体和公共领域视角对媒介进行的研究,另一种是将文化等同于“教育”的观点。“文化技艺”这一概念着眼于“文化”最本源的含义——“耕耘”,强调正是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技术和方法,塑造了时间与空间的范畴、内/外等一系列认知和区分,并将人建构成了特定的主体(Siegert 2015:3-5, 9-10)。鉴于此,梅田拓也(2012:304)将“文化技艺”概括为“先于各种文化而存在,并使这些文化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
文化技艺的特征之一是“通过使思维被感知,并将思维外化为可操作的对象,从而增强人类智能的运作”(Krämer&Bredekamp 2022:91),典型例子包括记谱法、十进制计算等技术。文化技艺论通过关注计数、测量、管理等实践行为,揭示了这些构成文化基础架构,却常被忽视的“不显眼的知识技术”(Siegert 2015: 2)的重要性。基于这一理论脉络,利亚姆·杨(Liam Young)进一步指出,“清单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工具性需求而诞生的,更是一个能在书写、思考和行动的过程中发挥能动性作用的物质性行动者”(Young 2017:25)。
以上述问题为出发点,下文将通过对放映列表(第2节、第3节)、演职员表(第4节)、排行榜及分集标题表(第5节)等方面展开分析,详细论述各种类型的“清单”是如何通过一种复杂而巧妙的方式塑造了整个动画文化。另外,需要说明一下,除了本文提到的这些之外,动画杂志上还出现过很多其他类型的清单,由于本文的目的在于展示相关研究方法的可能性,故只是选取了其中较为典型的几个案例进行探讨。
2.放映列表和计划性观看行为
《Animage》杂志早在创刊之初就独树一帜地将“清单”这一形式融入了版面之中。刊登在第一期杂志上的是一份完整收录了当时“日本全国播放的所有电视动画节目的总清单”(图4-1),被称作“全国放映列表”,并且在排版上采用了跨页的形式(『Animage』1978 年 7 月:46-48)。虽然是创刊号,但在专栏外面却标注了“为响应大家的需求”的字样。这表明编辑部在创刊前对动画迷进行过访谈,该栏目就是在调研过程中捕捉到的受众需求(大塚 2016:139-145)。此后,其他的动画杂志也纷纷效仿,开设了类似的栏目。这种跟风行为的后果就是“全国放映列表”成了一种动画迷们司空见惯的标配性内容。

创刊号的“全国放映清单”的一部分。《Animage》1978 年 7 月:46-48
“放映列表”乍看之下只是播送信息的简单汇总,无论是否存在,节目都会照常播出,因此显得无关紧要。不过,就像阿曼达·洛茨(Amanda D. Lotz)所指出的,正是各项技术的不断发展——从录制设备、电子节目单到允许在智能手机上观看的应用程序等等,使得观众拥有了更多观看自主性,让观看电视变得越来越便捷,由此导致电视接受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Lotz 2014),而“放映列表”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录像设备尚未普及的时期,电视节目一旦播完便很难再观看到。因此,需要根据收视时间相应地调整日常作息,而作为节目表的“放映列表”则恰恰是实现这一规划的重要媒介。虽然电视放送一直被塑造为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主宰性作用的“时刻表”,但却是在节目表出现之后,大众才真正意识到这一点。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放映列表”在信息处理方式上与传统报纸上的电视节目表有所不同。报纸是以“天”为单位,呈现每天可收看的节目;而“放映列表”则是按“月”列出全国各地电视台计划播出的所有动画节目,同时还会注明因节目播完而产生的节目替换情况。另外,由于“放映列表”是专攻“动画”这一类别,所以对动画感兴趣的观众无需费神从海量节目中进行筛选,可以省去不少麻烦。此外,相较于报纸上的节目表,“放映列表”的时间轴跨度长达一周甚至一个月,所以观众可以按“周”或“月”更长远地制定观看计划。
除了常规节目之外,“放映列表”中还包括动画电影等特别节目和重播信息。这些特别节目的信息会被醒目地标注在专栏之外。一般来说,电视台会在“固定的星期、时间段”持续播出同一类型的节目,如果观众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了在“固定的星期、时间段”收看某类节目的习惯,那么这种收视行为便很难发生改变。但特别节目通常只会播放一次,而电视节目的编排通常呈现规律的周期性特征,从这一点来看,特别节目属于一种例外情况。因此,越是习惯按照电视节目表来安排日常生活的人,就越有可能错过这些一次性节目。这个时候,栏目外的旁注就可以作为帮助观众应对规律日常生活中悄然出现的“意外状况”的一剂“良方”,提醒观众注意到并收看这些特别节目。
特别节目会播放平时收看不到的动画电影等作品。永田大辅曾指出,动画热潮的出现使得粉丝群体被划分为老粉/新粉,而区分两者身份的关键点就在于是否看过经典老番。同时,《Animage》等杂志也通过刊登各大电视台的动画放送年表、评选经典名作等方式,在广大粉丝中构建了一套公认的“动画史”体系(《Animage》1979年2月:61-78等)。另一方面,由于这个时期正值录像带普及的初期阶段,一旦错过了某部动画,就很难再有机会观看到。因此,播放经典动画电影的特别节目,便给新粉甚至是错过首播的老粉提供了宝贵的补番机会。观看这些经典老番,粉丝们不仅能够亲身追溯官方梳理的动画史脉络,还能形成一种将当下的动画文化置于该历史延长线上的视角。
对于想要观看重播的经典老番的观众来说,节目表也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在“放映列表”上标上重播标记,这样就会一目了然地与首播的节目区分开来。不过,在电视台数量多、节目丰富的地区,想要收看所有重播节目还是很困难的。因此,动画杂志会从众多重播节目中筛选出“必看”佳作推荐给读者。《Animage》便曾多次推出过重播节目的特辑,比如在“为重播献上花束”系列栏目中专门介绍各地正在重播的经典作品——如静冈第一电视台播出的《网球甜心!》――以鼓励观众收看(《Animage》1986年11月:113)。在“放映列表”与这些推荐文章的协同作用下,读者便会自然而然地生出“看什么/不看什么”的想法,也就是形成一种自主规划的主体性。
3.放映列表与“偏远地区”团体的形成
如上所述,由于“放映列表”收录了电视播送的“所有动画节目”,所以观众能够以“月”为单位制定观看计划。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覆盖全国的性质也带来了相应的阅读实践。与报纸的节目栏或电子节目表不同,“放映列表”汇集的是全国各地电视台播出的所有动画节目。这意味着读者不仅可以根据自己所在地区可收看的节目来制定计划,还可以确认其他地区在什么时候播放哪些节目。
正是这种覆盖全国的全面性,在除了实现个人层面的观看计划之外,还催生了各种社会实践的开展,并且带来了一系列新的体验(近藤2020)。比如促进各地观众针对获取自己所在地区未播送的节目展开交流。由于日本采用的是县级放送体制,各都道府县的电视台数量不均,所以各个地区播出的节目在总数上存在差异。这样就导致以东京、爱知、大阪为中心的广域圈之外的地区收看不到很多动画节目。基于这样的状况,编辑部于是便在“放映列表”的专栏外附上了这样一段标注:“即使你所在的地区看不到某些节目,来和粉丝同仁们一起打造一个片库也很有趣哟!!”(《Animage》1980年4月:64)。事实上正如永田所言,当时确实有很多读者通过投稿栏互相交换录像带。动画杂志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承担起了连接全国各地粉丝的桥梁作用。这表明节目表通过直观展现动画播出资源的地域分布差异,协调全国粉丝的供需关系,成为了一种构建起粉丝交流网络的媒介。
另一方面,在考察“放映列表”的媒介作用时,还需要考虑到杂志本身的媒介特性。这是因为“放映列表”说到底只是杂志中的一个元素,其存在的意义还在于它与其他文章和版面构成的联系上。比如前面介绍的“为重播献上花束”这个系列就是与节目表中的重播节目相关联的,也就是说杂志会通过多种形式呈现“必看”的动画作品。
包含节目表在内的杂志内容网络按照动画放送中心/边缘的界限,将杂志读者共同体又进一步分割成不同的集合体。动画杂志本质上是二次媒介,其内容主要建立在对另一媒介的动画的评述之上,原则上仅靠购买和阅读杂志,并不能完成关于动画的信息获取行为,读者还需要去观看动画本身,才能完成整个体验。但是,如上文所述,电视台播送的节目按照区域的不同可划分为“能收看/不能收看”的节目。这种情况就导致杂志上反复报道的热门动画,有些地区的读者可以同步进行“杂志阅读”和“节目收看”,有些地区的读者则无法实现这种联动。这样一来,在杂志对作品的评价加持与放送机会分配差异的两相结合下,对读者而言就不单单只是“能收看/不能收看”的区别,而是会形成“能收看的必看/不能收看的必看节目”的认知。
因此,即使同属“动画迷”这个范畴,其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机会差距。从下面的投稿可以窥探,在节目表和杂志报道结合形成的网络下,一种独特的空间感正在被悄然酝酿出来。
我深切地感受到,有很多动画没有在地方上播出,或者因为时间的关系而无法观看。
只能从杂志上了解动画,这不是太可悲了吗?(『アニメージュ』1979 年 9 月:107)
尽管“放映列表”中的节目一览表只是二维的平面文字,但杂志与放送状况的组合,却使读者的脑中自动浮现出一幅不平等的地理状况图。
这种显而易见的放送资源差异,很自然便能让人意识到粉丝群体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基于放送机会差距的多个群体的集合。正是这种差异,使得《Animage》的投稿区频繁出现有关“偏远地区”话题的讨论。处于边缘地区的动画迷们,在哀叹自己所在地区的媒介环境贫瘠的同时,又时常以此为梗自嘲,这样的举动逐渐便在原本毫无关联的不同地区粉丝之间培育出了一种新的共同体意识。有读者甚至在1982年向《Animage》投稿呼吁成立“偏远地区协会”,并且此后也陆续刊登了有关“偏远地区”的投稿。
我对在“我的Animage”上刊登的一封来自偏远地区的来信产生了共鸣。因此我呼吁成立“偏远地区协会”。协会内容如下:
①来自全国各地的“偏远地区协会成员”向“我的Animage”报告偏远地区的悲剧。
②“协会成员”必须为生活在偏远地区而感到喜悦和自豪。
③“协会成员”要毫不懈怠地寻找只有在偏远地区才能体验到的乐趣。
怎么样?全国超过一半的动画迷都是“偏远地区协会成员”!!!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个协会炒热吧!!(『アニメージュ』1982 年 7 月:116)
动画杂志上的各类文章报道,其内容均是针对特定动画作品的以见解性语言及图像构成的信息,是观众解读节目和丰富观看经验的重要“资源”。不仅如此,这些文章与节目表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一个信息网络,并且这个网络将构建动画文化的时间与空间可视化,从而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时空感。约翰·杜海姆·彼得斯(Peters 2015)将地图、时钟和高塔这类以特定方式将时空可视化并生成时空本身,从而将人或物置于特定时空框架下的存在命名为“后勤型媒介”。杂志上的节目表,正是通过与其他文章报道一同被收录、编排,发挥了类似的作用。
4.演职员表和“御宅族”的门槛
除了固定栏目的“放映列表”之外,动画杂志还会刊登许多其他“清单”形式的内容。比如收录参与每集制作的主要工作人员的“演职员表”。这种清单有时会作为报道的补充内容出现在杂志上,有时则会以汇总到一整个版面的形式呈现出来。动画本质上是集体创作的产物,基本上每一集的演出、脚本、主要作画者都会有所变动。演职员表正是为了记录这些流动更迭的动画“创作者”而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清单”的出现改变了观众欣赏动画的方式。下面我们来详细探讨一下。
说起来,为什么动画杂志会开始刊登演职员表呢?原因其实与前面提到的放映列表一样,制作人员的信息对当时的动画迷们来说也是一种极为迫切的需求。
冈田斗司夫(1996:11-12)和大冢英志(2016:152-160)均指出,在动画杂志和录像带尚未普及的年代,整理“演职员表”本身就是御宅族一项十分重要的活动。这是因为当时的媒介环境下动画很难被保存下来并反复欣赏。在录像带普及之前,较为普遍的做法是使用卡式磁带对动画节目进行“录音”,当时有很多粉丝通过杂志互相交换自己录制的磁带。甚至有人用相机对着电视屏幕拍照。正是这种渴望将节目储存下来的想法促使粉丝们通过各种手段把动画记录下来(大冢2016:115)。而整理“演职员表”便是这种记录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动画杂志刊登“演职员表”的这一举措,可以说不仅替粉丝们承担了手工整理的辛劳,而且让每个人都能轻松获取到“创作者”的信息[1]。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演职员表”不仅只是显示谁参与了制作,更重要的是,它使作品的视觉性开始有了另一层意义。要详细探讨这一点,首先需要了解电视动画作为一种视觉表达形式的特点。影像的运动本质上是基于静止画面的连续呈现,每一帧画面在播放时都是不可见的。但是,日本的电视动画采用的是有限动画形式,即每秒只有很少的帧数。因此,与真人版影像相比,动画的每一帧画面会更容易被肉眼捕捉到,并且创作者的不同会导致每一帧画面产生优劣之分。也就是说,动画的画面中被嵌入了“创作者”的个人印记。粉丝们在观看的过程中通过有意识地关注片尾滚动的演职人员信息,逐渐便能辨别出不同创作者的手笔(岡田 1996:12)。这样一来就可以在集体创作的画面里发掘出其中蕴含的“作者性”以及与其对应的“特定人名”(大塚 2016:152)。
“演职员表”就像一个透镜,通过它可以清晰窥见作品背后的“作者性”及其对应的“特定人名”。虽然即使没有这种名单,也能挖掘出创作者的蛛丝马迹,但若要顺着这些蛛丝马迹找到对应的具体创作者姓名,只能根据脑海中模糊记得的片尾演职人员信息去进行推测。即使粉丝之间试图互相佐证,也没有判断正确与否的标准。因此,将“作者性”与某个“特定人名”联系起来就会变得极其困难。“演职员表”出现后,粉丝们便能够将记忆中的图像纹理与参与制作的“特定人名”以及职能联系起来。在对照着杂志上的“演职员表”观看节目或追溯记忆中的画面时,就可以通过各个作品的演职人员差异与共性中逐渐辨明其创作特点。
不仅如此,“演职员表”可以说本身就塑造并巩固了一种观念——即“作者性”是与某些“特定人名”牢牢绑定在一起的。由于“清单”本身就是一种“压缩数据并最大限度提高纸张带宽效率的格式”(Young 2017: 39),因此不会列出所有参与制作的工作人员。正如杰克·古迪(Jack Goody)所述,“将单词(或事物)罗列成清单的行为,是在将某一部分内容纳入的同时排除其他内容,所以其本身就是一种分类方式,也是在划定一个‘意义范围’”(古迪 1986:193)。“演职员表”通常会更倾向于选择导演、作画监督、美术等职能。也就是说,有资格被称作“创作者”的仅限于与作品视觉风格相关的岗位,“创作者”这个头衔并不是所有参与制作的人员都可以平等享有的。
“演职员表”将每集(或每个)作品的“作者性”限定在了一组具体的、有限的人名上,正是这种明确化的归属,使我们能够清晰地对比出不同创作阵容之间的差异。“演职员表”是按照固定的项目类别收集和记录人员信息的清单。并且,类别及排列顺序会始终保持不变。这种形式上的不变看似理所当然,但在探讨名单的媒介作用时,却至关重要。正是因为格式不变,当人员信息被填入这个固定框架时,不同剧集之间的制作人员异同就会变得一目了然。如果连续几集的制作人员都不同,即使无意比较,这种变化也会自然而然地被人注意到,注意到这种变化的人于是便会产生一种微妙的异样感。当然,任意挑选某几集的演职员表去对比,也会很轻易发现其中的差异。
通过这种比较性的视角,我们可以很快确认创作者的创作风格。比如,某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所属一集的作画监督与其他剧集不同,那么该场景体现的“作者性”就可以很自然地归结到该作画监督身上。并且,如果我们在其他动画的演职员表中发现了这位作画监督的姓名,就能通过不同作品中展现的一致性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该监督一贯的创作风格。
西比尔·克莱默尔(Krämer 2003)在讨论书写的媒介作用时强调,书写不仅是信息传递的载体,更重要的是它能将信息空间化,从而使不同元素连接起来。“演职员表”正是这一理论的生动体现,它通过一一对应的列表形式明确地将各种关联呈现出来,让“作者性”与具体人名牢固地绑定在一起,使不同作品经由共同的“创作者”联结成的网络变得可视。而且,由于“演职员表”是有选择地列出部分职位,这样就导致大家不会去注意其他可能存在的演职员差异,进而让人产生一种只有名单内的差异才重要的认知。
冈田(1996:19-35)指出,被动画杂志和录像带所塑造的“现代御宅族”拥有“逐帧慢放深入解析的视角”、“强大的考据能力”、“永不满足的上进心和自我表现欲”,他们通过与其他受众不同的“专业之眼”对动画进行鉴赏。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就是他们可以根据画面中描绘的内容迅速推测出该场景是出自哪个创作者之手。而“演职员表”正是培养出这种“专业之眼”的关键,并且赋予了这种眼光以价值。它不仅定义并塑造了“御宅族”这一身份本身,更是构建动画文化的一项关键性文化技艺。
5.作为一种记忆装置的排行榜
最后,我们来探讨一下按照特定标准对一组对象进行排序的排行榜形式的“清单”。在日常生活中,这种类型的清单比较常见的有基于销量和播放次数的音乐排行榜、电视收视率排行榜等。在制作动画时需要重点关注DVD和蓝光光盘销售额的时期,这些音像制品的销量榜不仅对内容制作方和受众双方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也被视为一项衡量作品人气的指标。
除了这类排行榜之外,类似的还有《Animage》从1979年起每年举办一次的动画大奖赛,这项赛事根据读者投票情况从多个维度对动画进行排名,最后公布结果。虽然没有具体的榜单,也能从杂志特辑中看出哪些作品备受推崇,但却无从知晓读者群体内部什么作品最受欢迎。同样,如果没有榜单,即使知道哪几部作品在粉丝圈子里比较热门,但没有排名便无法确认这些作品的人气高低。这种对热门作品进行排序的排行榜,既可以在无形中引导读者群体形成一种共同的审美取向,同时也可能因排名差异而引发争议,激起读者进行热烈的讨论。
动画大奖赛成为一项常规活动后,无论是否参与投票,观众都会纷纷预测哪些作品能上榜。比如对于动画大奖赛中“历届最佳作品”这个奖项,1985年时有读者就以“年度盛事!!!动画大奖预测”为题进行了投稿,并认为《高达》胜算最大。这是因为同年3月开播了续作《机动战士Z高达》,再加上“有些地方正在重播《高达》原作”(《Animage》1985年4月:135)[2]。另外,将动画大奖赛设定在年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观众养成一种边追番、边在心中给作品排序的观赏习惯。
这种排名类榜单本质上是一种操控记忆的媒介——它通过将少数上榜者捧上神坛,赋予其一种“值得被铭记”的光环,同时将未上榜的、排名靠后的作品排除在视野之外,使其陷入被大众遗忘的境地,从而起到操控大众记忆的作用(Straw 2015)。同理,“动画大奖赛”也将特定的电视动画作品打上了“值得被铭记”的标签。另外,这种榜单还会带来人气排名的更迭,并且给动画的评价体系增添一个类似“之前的排名”这样的“回顾性维度”(Young 207: 51)。比如开始流行起“连续X年位居前三”这类基于持续性热度的评价,由此便形成了一种新的作品价值评判尺度。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奖项是“最佳剧集部门”。这个奖项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是针对整部系列作品,而是针对单个剧集的制作水准进行投票评选。《Animage》杂志会将作品的各集标题专门刊登出来,以引导读者根据单集质量进行投票。如前所述,明确标注各个岗位人员分工明细的“演职员表”是动画杂志上的一个常规栏目,而这份名单在刊登时是需要以“哪一集由谁负责”的形式展现的,从这一点来看,“演职员表”其实就相当于是分集标题目录,所以动画迷们对于分集标题的信息可以说早就了然于心了。比如铃木克信就曾以“清单”的形式整理收录各个动画作品的分集标题和播出日期,出版了一本名为《电视动画播放列表》的同人志,由此在粉丝圈中名声大噪(大塚 2016:152-153)。
将各集标题整理记录成册,不仅是将整个动画分解成逐个剧集的形式记录下来,同时也能让观众将动画以“集”为单位留存在记忆中。对于无法随时保存、又动辄需要耗费数月甚至更久才能看完一部动画的追番过程而言,靠大脑记住所有剧情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事。就像当我们追完一部动画,回头品味整个故事时,虽然往往脑海中会浮现各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和经典台词,但对它们之间发生的先后顺序和承继关系,却常常会不可避免地感到模糊不定。
但是分集标题却能够以特定的方式使人忆起某个剧集的内容。并且这些分集标题以“清单”的形式呈现出来,可以让观众更好地区分、引用和讨论各个剧集。克莱默尔(Krämer 2003:521)强调,诸如目录、索引之类的“书写图像性”元素具有构建书籍内部认知秩序的作用。同理,分集标题就相当于书籍中的章节标题或索引,而分集标题表就相当于书籍的目录。分集标题表就像电视动画的目录,为观众容易变得模糊的记忆引入一条清晰的时间线,将记忆中散乱的画面与声音按集进行归类整理。不仅如此,它还明确了各个情节之间的先后顺序与承继关系,让观众在把握作品全貌的基础上,能够基于播出的时间脉络来解读整部作品。
《Animage》举办的“动画大奖赛”正是基于分集标题及其“清单”的特性,引入排名元素设立了“最佳剧集部门”。这种排行榜在让观众能够识别不同剧集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投票、排名的方式对各个剧集进行价值评判。一旦哪个剧集上榜,就会获得超越其他剧集的价值加成,也就是会被贴上诸如“经典”、“名场面”等的标签,进而成为观众们优先回忆的“特权对象”。这种排名机制的建立同时也是在粉丝群体中创造“共同语言”的过程,使得大家能够直接使用分集标题进行沟通交流。比如对于《高达》,有读者在投稿中曾表示“因为错过了12话,所以希望剧场(版)中能收录这集内容。非常期待看到夏亚戴墨镜的样子”(《Animage》1980年12月:22),这条投稿的成立便是建立在粉丝群体普遍知晓“夏亚戴墨镜”这一经典场景出自第12话的前提之上。之所以能够直接用分集标题来指代一段具体的情节内容并实现有效交流,正是因为这一集在粉丝群体中已经形成了广泛的知名度。
6.清单的“轻便性”
上文主要探讨了两类清单:一种是动画的播出时间、制作人员信息、分集标题表等可被称为“书目信息”类的清单;另一种是读者参与创建的排行榜形式的清单。实际上这些资讯在动画杂志出现之前便已经存在了。在此之前,大众可以从报纸等渠道搜集到相关情报,或者个人整理并记录下来,另外也可以通过同好团体内部进行投票评选的方式产生结果。这些形式的内容本质上都是一种文化技艺,它们系统地塑造了人们接触动画的方式,并由此催生出了独特的时空感,以及内/外意识。
以《Animage》为代表的动画杂志本质上是将20世纪70年代起就已存在的“文化技艺”系统地整合到杂志的内容编排中,并进行再传播的媒介。这类杂志诞生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将过去仅在特定圈子中流通的、外人难以获取到的资讯清单,以及个人耗时费力、极难系统整理的资料,作为商业出版物以低廉的价格持续提供给了广大读者。该杂志在创刊三周年之际发表的回顾发展历程及贡献的特辑中也特别指出,“地方获取资料比起东京要难得多”,因此动画杂志“对地方粉丝来说格外珍贵”。同时“将资料通过纸质媒体公开传播,意味着持有相同资料的人群规模等于杂志的发行量。这种情形不得不说十分令人震撼”(『Animage』1981年7月:99)。
清单是一种高度压缩的信息形式,具有能够轻易跨越不同媒介的“轻便”特性(Straw 2015: 136)。记录在纸面上的清单无需阅读设备,可以通过张贴、复印、归档或传阅等方式跨越时空的限制广泛传播。杂志的大量复制传播无疑又会进一步加强这种“轻便”特性。这样一来,资料的稀缺性就会不复存在,普通人要想掌握“御宅族”那种通过各类资讯清单练就的必备技能,其门槛也就大大降低了。
如上所述,动画杂志通过整合已有的信息以新的形式进行二次传播,使得任何人都能轻易获取到这些信息。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动画杂志塑造出了一种没有它就不可能存在的动画文化形态。动画文化并不是在动画出现后自然而然就形成的,而是有赖于围绕它的一系列文化技艺被系统地组织起来,才得以形成如今我们看到的文化样貌。“清单”这类事物看似微不足道,但正是这种“不显眼的知识技术”,以及孕育这些技术的特定历史社会背景,才是动画文化的根基所在。
【附记】:本文是以近藤(2020)、(202a)、(202b)中涉及的“清单的媒介性”部分为基础,结合新的资料和研究视角重新展开的分析讨论。
引用・ 参考文献
梅田拓也, 2022,「文化技術とコンピュータ」『現代思想』50(11), 162–172.
岡田斗司夫, 1996,『オタク学入門』太田出版
大塚英志, 2016,『二階の住人とその時代――転形期のサブカルチャー私史』星海社
グディ, J., 1986, 吉田禎吾訳,『未開と文明』岩波書店
近藤和都, 2020,「アニメブームのインフラストラクチャー――『機動戦士ガンダム』をめぐる放送
格差と雑誌読者」永田大輔・松永伸太朗編『アニメの社会学――アニメファンとアニメ制作者
たちの文化産業論』ナカニシヤ出版, pp. 189–203.
近藤和都, 2021a,「﹁ヤマト﹂から﹁ガンダム﹂へのメディア史――﹁記憶すべきもの﹂と﹁記憶す
る人々﹂」荒木浩・前川志織・木場貴俊編『〈キャラクター〉の大衆文化――伝承・芸能・世界』
KADOKAWA, pp. 301–324.
近藤和都, 2021b,「『機動戦士ガンダム』と(再)放送の文化史」大塚英志編『運動としての大衆文
化――協働・ファン・文化工作』水声社, pp. 167–181.
佐藤健二, 2015,『柳田国男の歴史社会学――続・読書空間の近代』せりか書房
クレーマー, S., & ブレーデカンプ, H., 2022, 遠藤浩介訳,「文化、技術、文化技術——文化の言説化
に抗して」縄田雄二編『モノと媒体の人文学——現代ドイツの文化学』岩波書店, pp. 80–95.
Gitelman, L., 2014, Paper Knowledge: Toward a Media History of Documents, Duke University
Press.
Krämer, S., 2003, A. McChesney,(trans.), Writing, Notational Iconicity, Calculus: On Writing as a
Cultural Technique, MLN, 118(3), 518–537.
Latour, B., 1990, Drawing Things Together. M, Lynch,, & S. Woolgar(eds.), Representation in
Scientific Practice, MIT Press, pp. 19–68.
Lotz, A., 2014, The Television Will Be Revolutionized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eters, J. D., 2015, The Marvelous Cloud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iegert, B., 2015, Winthrop-Young, G.(trans.), Cultural Techniques: Grids, Filters, Doors, and
Other Articulations of the Real,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Straw, W., 2015, Mediality and the Music Chart, SubStance, 44(3), 128–138.
Young, L. C., 2017, List Cultures: Knowledge and Poetics from Mesopotamia to BuzzFeed,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注释:
[1] 因本文篇幅所限无法详述,但在演职员表的制作与流通方面,有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就是被称为“数据原口”的原口正宏(大塚 2016:444-461)。
[2] 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是哪里在重播,不过对方应该是从放映列表中确认了有重播地区。







还木有评论哦,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