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人们质疑文明本身就是堕落之源,堕落不但滋生了肉欲和暴力,还使性欲和暴力成为人们的避难所,让人们得以排遣对于日常生活的既成事实的厌倦。”
1900年前后,柏林和维也纳一方面是科学知识、理性与现代化的中心,另一方面是滋生堕落与衰败的温床——鱼龙混杂的大都市充斥着贫困、犯罪和暴力。《启蒙与颓废:世纪末时期柏林和维也纳的地下世界》一书所要探讨的就是这一矛盾的图景:极端堕落的幻想是如何融入作为进步文明之中心的中欧城市的自我形象的?作者从世纪末的维也纳和柏林切入,试图解析一个福柯式命题:新兴的精神病学、性学和犯罪学等科学如何塑造各式社会边缘群体?作者广泛运用了当时的科学论文、新闻报道、警方调查、法庭文书等多种文献,辩证地剖析了启蒙与颓废相交织的现代性之复杂。本文摘自该书第一章,澎湃新闻经拜德雅授权发布。
近现代大都市的生活和此前的一切生活形式是否截然不同?这种区别是如何形成的?这种差异是何时成形的?人们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上述问题遮蔽了一个真正的历史问题,一个更加引人入胜、更加复杂难解的问题:认为“近现代大都市的生活和此前一切生活形式截然不同”的这种思维方式本身是如何产生的?这种思维方式发挥了哪些作用?当代城市世界是完全的创新、空前的希望、隐蔽的极端危险,如果这些假设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是虚构的,那么这些想象的影响却是真实而显著的。人们在中欧德语国家和其他地方都围绕这一议题创作了数量众多的文化作品,从新的视觉艺术作品和建筑,到文学体裁、新兴学科、专业机构以及研究领域。
即使人们为世纪末下严格的定义——世纪末指从19世纪90年代前期到大约1905年的这一短暂时期,他们仍然难以限制那些在人们看来也许对上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的再现和实践的数量;我们需要辨识相关文化内容的主题。这些文化内容中的一个概念是近代城市的形象,或者所谓的“大都市”(Großstadt)。大都市是人们思考现代性的体验的前所未有的特点的中心范畴。一方面,人们自我肯定,对文明和进步充满自信,另一方面,人们对衰退、疾病和危险充满恐惧,感到焦虑。在大城市里,人们可以找到积极的看法和消极的观点的根据。社会对“全新的”大都市带来的威胁和给人的期盼(黑暗和光明)的文化想象凸显出一系列对立关系——城镇和农村、文明和自然,等等——有些对立被遮蔽,有些对立被揭露。犯罪和城市具有如此密切的关系,犯罪的形象就是在这种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以至于人们有时认为犯罪和城市似乎是互相依附的关系;人们对犯罪之本质的反思经久不衰,争论不断,这便是黑暗和光明相互交织的城市景象的镜像。
我们准备了一个实用的工具箱,这些工具的用途是分析这些迥异的事物。我们会利用这些工具处理一些不同的现象。在很多时候,这些现象似乎催生了那些最有创造力的时刻,那些在人们眼中必然会被视作一个革命性的文化产物的时刻。我们的调查指向下列对象:地点(location),这是指犯罪在城市中的地理分布和对犯罪源头的搜寻;认同(identification)和身份问题,这和地点的概念有关;在修辞的层次上,我们关注讽刺(irony),这是指悖论或对立的双方的联合;体裁(genre),这是指小说创作,其诞生是为回应各种新鲜的情况;程序(procedure),这是一种对方法和体系的关注,同时一种要扬弃此前的传统程序的冲动。
大都市的悖论
黑暗和光明的对立是1904年汉斯·奥斯瓦尔德(Hans Oswald)的《柏林的黑暗角落》(Dark Corners of Berlin)的重要内容,不过,作者为那些黑暗的角落涂满了色彩。“柏林最黑暗的角落之一是奥拉宁堡门周围,那里有着最明亮的彩灯和最多彩的活动”。作者提出了一种深刻的洞见,“黑暗的行径并不总是避开灯光的照明”,这是用灯光照亮街道的原因,也是他期望中的他的著作的目标。“我们的现代科学,”奥斯瓦尔德指出,“我们的现代前景方兴未艾,人们不能自信地放任自己直视那些至今仍被我们视为禁忌的事物。”人们对“黑暗的城市”的痴迷所包含的部分矛盾与启蒙思想对“包括知识和未来在内的现代性的胜利”的自信有关,因此,人们无法冷静地看待此前的某些事物,它们过于丑陋,人们无法直视。《柏林的黑暗角落》是后来出版的一系列被统称为“大都市档案集”(Großstadt- Dokumente)的学术著作(共51部)中的第一部。根据奥斯瓦尔德的说法,这些学术著作的作者和编辑的目标是“阐明”这些黑暗的角落,提供“走出大都市迷宫的向导”。在这些著作中,各种各样的专家学者引导好奇的读者走进近代特大城市的混沌。不过,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无法言说的混沌状态——卖淫和嫖娼、变态行为和性别错乱、赌博、猥亵行径、玩世不恭这些事物。人们在那些巨型城市里找到了这些黑暗角落。上述的禁忌不是一种古代的禁令——禁止人们说出永远不可言说的事物,而是另外一种禁令——禁止人们说出文明的另外一半,这种禁令既是现代文化的产物,又是科学和艺术的产物。该系列丛书的另一位作者如此看待这样的现象:“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柏林不是一夜建成大都市。”如果巴黎是19世纪的光明之城,那么人们达成的世界共识就是,没有一个城市的夜晚比柏林的夜晚更有魅力。除了这些文章中常见的巴黎和伦敦的比较,作者还回顾了古代罗马和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名城,不过在这些作为世界文化之明灯散发无限光明的高光时刻,柏林带给人的“感官快感”仍超过了它们。如果近现代大都市是文明的最高点,那么它亦是世界历史的恐怖小说的场景。
人们对文明进步感到骄傲,对城市的地下世界这一特定空间感到厌恶(可能还感到错位的亢奋),这两种情绪的并存并不是一个人们闻所未闻的现象。德意志的霍亨索伦王朝时期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后期——在英国和美国等英语世界国家,人们把该时期称为“维多利亚时代”——这两种情绪的并存是当时人们的刻板印象之一,人们显然不认为这是一种矛盾的现象。不过,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复原和审视这种可能自相矛盾的怪象:乐观主义者主张我们的文明已经进步到一定的程度,文明已经开始面对文明自身的退化状态了。与日俱增的图片和文字是以近代城市为具身体现的衰退时代的证据,该时代的伴生现象是一系列对“现代性能够治愈现代性造成的伤害”充满信心的其他体裁、仪器、学科和机构。这些冲力(impulses)之间密切而复杂的关系意味着人们不能通过分开或拆散这些冲力,从而区别每一种冲力。奥斯瓦尔德利用表面上具有科学性的冲力来理解城市生活柔软的腹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隐蔽的对轰动效应的追求。
如果人们试图把城市故事视为严肃的事物,而不只是病态的父权家长制文化的症状,那么他们可以从对城市故事中的淫乱活动的文化意义的分析中发现些什么呢?这些文本和实践可能产生哪些积极的影响?人们可以把它们视为规范性的管制机制和边缘化手段的全新形式吗?如果把这些现象的功能视为社会控制,那么就会存在低估这些现象的风险,正如我们第一次在这些文本中读到这些城市本身时低估了它们一样。例如,一种解释认为:这些文本的主要作用是将“他者”污名化,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解释只会导致人们重复和这些文本及其作者一样的粗糙的污名化。
破解关于犯罪、性爱和大都市的文本系统的复杂性,其最重大的方法论问题之一是研究者难以在避免简单重组这些文本的情况下分析这些文本。不难想到,我们很难不在关于中欧的大城市的讨论的章节开头首先讲述19世纪后期的物质条件的变化。这些物质条件的变化造成柏林、汉堡、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等城市成为近现代大都市:国内人口的城市化;大城市的人口增长;电气化进程、通讯革命和交通革命;报纸媒体的爆发,等等。有关大城市的话语的历史似乎在结构上和此种说法的再生产绑定在一起:突然之间,生活真的不同了,当代人的生活和此前历代人体验的生活方式不同了。在当时的讨论中,人们引用最多的文本一定是柏林的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长篇讲座《大都市和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齐美尔确信无疑、洞若观火地主张:显而易见,近代城市生活不同于此前的生活方式。他的论文中满是名言警句,这些名句似乎证明了一条因果链条:
大都市是全新的物质条件的产物,全新的物质条件形成全新的生活方式,全新的生活方式造成独特的感官体验,独特的感官体验对主体带来空前的影响。齐美尔有一句令人难忘的话:“大都市的个性的心理基础由神经刺激的激化(intensif ication of nervous stimulation)组成,这种激化是外在和内在刺激(stimuli)的快速而持续的变化的结果”。但是当人们把这场讲座的因果链条抽取出来时,他们注意到了暴力在修辞学上的力量和影响。人们认为这篇文章不是社会学的学术研究,或者至少后来的社会学家认为这篇文章的论证“不成体系”,因为齐美尔排斥方法论的主张和他的观点明显前后不一致。文章的二分法的核心是近现代大都市的生活和文中所谓的城镇或者农村的生活(他把二者混为一谈)。但是二元的范畴是不稳定的,各种因素都会带来变化,包括:古代城市和现代城市、前大都市的大型城市、自然条件,等等。并且大都市的特性(从劳动分工到便捷的通信)通常是广义上的现代事物,许多地方的居民也能共享这些现代事物,它们包括但不限于相对极少数的特大城市。人们认定这些城市是大都市。在这篇文章中,城市既是原因,也是结果,既是产品,也是生产者,既是现代文明的产品,也是造成城市居民发生变化的压力来源。这种环形结构的中心不是城市,而是现代的主体。这种环形结构的地位高于作者似乎在各种各样的论点上提出的因果观点和线性观点。虽然该文的英语译者通过编辑段落,把这篇讲稿改编成了一篇论文,但是最初的文本的内容是一系列论点或格言,分号和破折号隔开了从句的链条。人们宣称,这篇讲稿的内容是受到过度刺激的、注意力分散的理智主义思想(intellectualism),作者把这种理智主义描述为现代城市主体的条件。显然,这种诊断并没有超出齐美尔自己的洞见和意图。虽然这篇文章存在自相矛盾和讽刺之处,但是无论如何,作者提到了个体的“基本动机”,这与马克思和尼采的观点相同,即“社会-技术机制(socio-technical mechanism)中的主体的抵抗逐渐下降,消耗殆尽”。
人们用“对立统一”的比喻来描述齐美尔的特大城市悖论。人们对中世纪神学和哲学的心理学分析拯救了这个概念。齐美尔认为,启蒙运动发生以后,普遍主义和个人主义双双走向极端化和公开化,城市是普遍主义和极端主义之间的更加宏大的冲突的场域。起初,大都市本身是全新类型的主体聚居区的物质体现。众多相互冲突和彼此共存的冲力是一种全新的种类的主体的发明创造的产物。
我们可能会认为,齐美尔的观点是对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的说法的提前修正。米歇尔·德·塞托认为,城市是互相对立的观点和体验的具身体现:其中一种体验是自上而下,以客观、抽象而科学姿态俯瞰城市;另外一种体验是人们漫步街道的所见所闻的丰富性和迥异的城市的和谐统一性。“概念城市”这个人们创造的理论概念在技术进步使人们得以亲眼见证它之前便已得到了可视化处理(这种可视化凭借由数字计算推动的启蒙运动视角而得以实现);“概念城市”不但是一个不同的地方,而且是一类不同的地方,其来源是人们漫步城市之中时的体验到的不规则性、和谐统一性和多元性等现象。这些现象似乎不但是不同的知识的组成元素,而且是对立种类的知识的构成要素。我们在阅读齐美尔对大都市的论述时,通过提出一个不同的问题,来批判这种对立:如果在我们所研究的那个时代,这两种观点完全意识到了对方的存在,会怎么样?如果“概念城市”和“街头体验”、规划严整的城市和所谓的“黑暗”城市原本就是一体,会怎么样?
类型化的城市:书写大都市
城市的地下世界有着引人注目的风景,这是一个严格区分了对世纪之交的大都市的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的问题之一。描绘城市时撇开罪犯、娼妓和堕落者就像描述农村时撇开土地。这种两难的案例可见于《柏林生活每周评论画报》(Illustrrite Wochenrundschau über das Berliner Leben)。这是一本发行于柏林的周刊,其目标是报道德意志帝国的全新首都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积极图景。杂志的第三期刊登了A.冯·泽布斯特(A. von Zerbst)的关于城市犯罪活动的文章,作者对于城市犯罪的解读不是理性思考的产物,而是自信情绪的产物。第一,泽布斯特主张,实际的犯罪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幅增长,因为城市犯罪的增加和城市人口的膨胀是成正比的。第二,他引用了一位学者的说法论证如下观点:自然经济的循环证明,犯罪活动的增长实际上是德国统一所促成的经济繁荣的结果(因此犯罪是国家成功的一种标志)。最后,作者转而用大量文字以描述一种日益发展的大众文学体裁:“后梯小说”(backstairs novel),这种廉价的小说的本质是一种刺激感官的猛料,期间“充满最疯狂、精密和可怕的犯罪活动”,作者通常是通过连载的方式在号外刊上读到这些故事的。杂志编辑宣称,一些不道德的作者和出版者的动机是牟利,他们的作品的主题总是关于城市的犯罪案件,编辑们对此颇有微词:“人们的幻想被激发了”。泽布斯特从人们的幻想跳跃到社会现实,他隐藏了自己对他描述这种新型的追求感官刺激的猛料式体裁的立场。不过他这两个行动都没能成功。
描写城市黑暗面的感官猛料式的文本大幅增加了,这一点普遍为人所承认,并且人们承认的方式往往是那些又再生产了他们所报道的感官猛料式的文本的色情趣味(就像泽布斯特的文章那样)。人们在各种地方看到这种趋势,从低俗小说到犯罪报纸,从警方通告到主流媒体。正规报纸对猛料的报道比大众媒体更加敏锐。报纸使用的《谋杀?柏林最黑暗的角落的一起神秘事件》等标题与犯罪小说产生了共鸣。文章作者制作有问题的城区的地图,引导读者穿行于特殊的黑暗角落。这些文章中的地下世界丰富而多元。潜在的暴力活动带有混沌的随机性,但是包含有层次和有规律的细节。泽布斯特在他的文章中暗示,柏林的犯罪活动是近现代的大都市本身的反映。柏林是前所未有的人类活动和生产活动的领域:“所有的犯罪活动都在巧妙地扩大犯罪的体系,这种扩张对公众而言既是有趣的,又是危险的,因为个别罪犯难以实现扩大犯罪体系的目标,它必须依靠许多帮凶的支持。”后来同一画报的另外一期的一则报道提供了一份柏林的各种监禁机构和监狱囚犯的全面报道。
这些监狱的高墙之下的社会体系让人们联想到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的森严等级:每个社会机构都有自己的代表,各种职业对应各种犯罪,各种囚犯受到各种惩罚。邮差和法官对应挪用公款;教师对应强奸和禁锢;商人对应诈骗;屠夫对应伤人;面包师对应赌博;仆人对应盗窃;最后,侍者对应那些勾结群众的犯罪者。监狱巡礼是窥探城市阴暗面的典型文本。报道既展现不为人知的世界,也揭露已知世界的秘不示人的本质:官僚和经济生活的腐败,教育系统的虐待;世界的卑鄙、淫乱和贪婪。这是读者已知的世界的特点,也是读者未知的世界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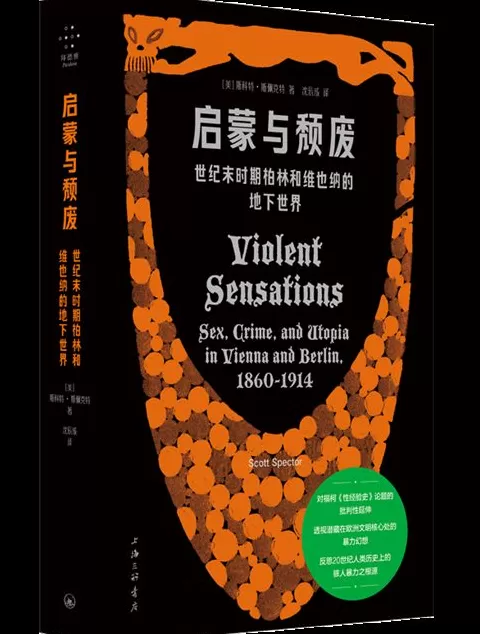
《启蒙与颓废:世纪末时期柏林和维也纳的地下世界》,[美]斯科特·斯佩克特著,沈辰成译,拜德雅×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8月。







还木有评论哦,快来抢沙发吧~